艾芜抗战小说的巴蜀文化气韵
2024-06-24 10:19:14 来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5期 P21-27 作者:陈思广, 刘笛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艾芜的抗战小说具有浓郁的巴蜀文化气韵。如《山野》在艺术手法上,作家或通过叙述者对叙述手法与叙述时间的控制,即通过插入停顿、重复叙述、倒述等手段,改变文本的叙述时长,形成缓慢匀缓的速度与节奏,契合巴蜀之人安逸闲适与自由散漫的性情;或以简单的几个人物勾画出一场耿直燥辣、爱恨分明,充满激情的山地战,映现巴蜀儿女耿直燥辣、爱拼敢闯的人物性格。在人物塑造上,艾芜以蜀地民兵、荣归军人、逃兵以及难民等,构成了其抗战小说的人物全图,其中,又以荣归军人塑造最具特色。在小说意象的营建上,艾芜选取了具有典型巴蜀文学气韵的“洄水沱”意象,将表面上缓和平静,实则暗流汹涌,汇污积垢、杀机四伏的巴蜀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艾芜的抗战小说呈现出特有的巴蜀文化气韵,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艾芜;抗战小说;巴蜀文化气韵
谈及艾芜,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他的《南行记》,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将“漂泊”“流浪汉”“浪漫主义”等词语集艾芜于一身,这固然反映了艾芜留给读者的深刻印象,但我们也想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出读者对艾芜创作理解的偏疏。因为艾芜不仅是一位“漂泊作家”,一位“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开拓者,还是一位抗战小说家,一位巴蜀文化气韵的自觉践行者,特别是当我们整体审视艾芜的抗战小说时,这种感受显得愈发强烈而清晰。
一、《山野》的游击战书写与巴蜀文化气韵
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独有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巴蜀人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模式,并造就了相对富庶、宽松的生存环境,同时四面环山的地理环境在过去通讯落后的条件下无形中阻隔了国家权力、国家文化对巴蜀地区的渗透与束缚。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巴蜀文化和其经济模式一样,在国家文化(儒家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自给自足地蓬勃发展。这就势必会形成一种安逸闲适、自由散漫的生存景观,形成“文化性格上相对保守、封闭,缺乏努力创新之激情的特点”[1]18。但燥辣、耿直的“巴蜀性格”,少受礼教纲常桎梏而可以较快接受新奇事物、文化的特点,又使四川人往往敢于冲破盆地的封锁,去追求和获得更为广阔的视野与价值观,并以之作为逻辑基点来反观、自省本土文化之优劣。所以,一面是安逸闲适与自由散漫,一面是耿直燥辣与爱拼敢闯,共同构成了巴蜀之地的文化气质之特点。表现在《山野》中,就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通过叙述者对叙述手法与叙述时间的控制,即通过插入停顿、重复叙述、倒述等手段,改变文本的叙述时长,形成缓慢匀缓的速度与节奏——这恰与巴蜀之人安逸闲适与自由散漫的性情相契合。《山野》的故事是描写吉丁村在一天一夜里的抗日游击战生活。这看似短篇小说的题材,但艾芜硬是写出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巨制”。那么,艾芜是怎样控制文本时间使其形成“长制”呢?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就是穿插停顿。例如在16章结尾处,写美珍和阿栋离开“军营”,开始返家。21章写阿岩与村长韦茂和失和,气愤地夺马,准备和阿龙离开吉丁村。到了23章的时候,骑马离开的阿岩和阿龙才遇上从“军营”往家回的阿栋和美珍。也即是说,小说的第17~22章实际上是一个信息量庞大的穿插段,利用的就是美珍和阿栋从“军营”返家的这段时间(16~23章),这段回家之路在文本中完全没有提到,也就是说,没有预定情节,作家全部用来作为其他事件的穿插。对于文本设定的一天一夜的总时长来说,这一段“返家时间”所占用的比例很小,但所叙述出的情节量却非常丰富(当然还有一个不宜重复计算的21~23章之间的小插入)。同样的例子还有,第22章末尾写徐华峰提出与韦茂和同去黑虎关查看情况,第25章才写他们到达了黑虎关。中间的第23章就是一个插入(24章为倒述)。从第26章开始直到第28章(第二部结束),都是描写吉丁村的民兵与敌人作战的场景,第27章交待阿劲、阿树受困,第28章交待徐华峰生死未卜,第三部的29、30(部分倒述内容)、31、32章则又是一个多内容的插入,直到在32章的“下半阙”三人分别被阿龙找到(中间省去了阿劲和徐华峰是怎样脱困,阿树是怎样死亡的情节,只用美珍与美玉去前线的情节取而代之),文本的叙述时间得以延长。除了插入停顿外,倒述也是延长文本时段的好办法。从第5章伊始,叙述者先用了一个不太标准的技术性重复,即运用韦茂廷的视角简要重复了第4章韦茂和与长松见面的事件,随后就以倒述的方式,讲述他和长松、长桃两兄弟的过节。第11章长松给美珍和阿栋介绍矿工队的历史、第30章倒述美珍从野猪岭回来以后办托儿所的事宜等,也是如此。倒述所起的作用就是补充历史信息,让情节或人物像在开始叙述之前就真实存在,一直延续到现在一般,省去了花费正叙时间去描述不太重要的补充信息的叙述时长。如果没有穿插和重复或是倒述,完全按线性时间来叙述的话,《山野》或许会因为没有起承转合,没有悬念设置,没有欲扬先抑而变得味同嚼蜡,难以下咽,但这与巴蜀之地重趣味逸致的文化性格也显然不符。因此,表面看来,这是艾芜处心积虑地运用多种叙述手法拉长一个原本并不复杂的故事,实际上是巴蜀文化气韵潜移默化的结果。
(二)以简单的几个人物勾画出一场耿直燥辣、爱恨分明,充满激情的山地战,刻画出巴蜀儿女耿直燥辣、爱拼敢闯的人物性格。小说写的是一场游击战,战斗开始时,阿树和阿劲正准备去巡逻,原本指望着阿岩带领队伍打响伏击战,但由于日本鬼子出现太快,阿岩的队伍正在陈家镇截击另外的敌军,阿劲、阿树、阿寿便与敌人展开了近身战。不久阿寿牺牲,阿树被击中手臂暴露了位置,陷入与敌人的肉搏之中。千钧一发之际,阿劲顾不得浑身的划伤,从死亡线上将阿树救回,这种在生死线上本能地爆发出的耿直侠义的战斗精神,就是巴蜀文化气质中耿直燥辣的具体呈现。随后,阿劲考虑到阿树的伤势以及心理创伤(差点被敌人扼喉管致死),让阿树赶紧离开,留他自己与敌人抗衡:
阿树听见阿劲这么地说,便又不忍地低下了眼睛。
“那么我也不走了!”
“不可以的,你带伤了!”
阿劲坚决要阿树走开,一面偕抬头往上面瞧了一瞧。阿树抬起头来在惨痛的神色中,竭力鼓起勇气说:
“没相干!我右手还可以用手枪打仗。”
“不成!”阿劲迅速地摇一下头。“你一定走吧!”接着又指一下阿树手里拿着的手枪,“你这点子弹打完了又怎么办?快点走了吧,你留着,倒使我担心!”[2]309-310
阿劲和阿树既是战友又是朋友又是哥弟,他们互相体谅,粗中有细,又互相角力,敢爱敢恨,虽都不言明,但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愿意为朋友为国家牺牲,像是两个耿直仗义、充满豪侠之气的孤胆英雄。仗义豪侠的孤胆英雄还得算上小知识分子徐华峰,当他得知阿劲、阿树和阿寿身陷险境,又被阿栋拒绝援救后,一激之下带着另外三个战士前去支援。徐华峰只是一介从未玩过枪杆子的书生,在危难关头不计后果地自告奋勇,就是一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拥有这种耿直精神的还有阿岩,因为贫困,阿岩一直被吉丁村许多人物所排斥,他几乎是半逼迫着离开吉丁村投靠了长松的矿工队,但他还是愿意救吉丁村于水深火热中。正是艾芜将深植于心的巴蜀大地的生存体验、川人特立独行的文化性格,融会贯通在他笔下的正面人物灵魂中,才使他们的性格既活灵活现,又透发着浓郁的巴蜀文化气韵。
二、民兵、荣归军人、逃兵与难民:艾芜抗战小说的人物形象
艾芜抗战小说的巴蜀气韵不仅表现在艺术手法与巴蜀气质的高度契合上,还表现在艾芜对蜀地民兵、荣军者、逃兵以及难民的形象塑造上。这几类人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艾芜抗战小说的人物全图。
民兵是一种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组织。《山野》中吉丁村的民兵们都是当地的农民,他们没有精良的装备,也没有受过正规军的素质训练。时代的巨轮将他们推到抗战的最前线,他们只能放下锄头,扛起刀枪,保一方水土。只不过,他们的爱国主义意识较为淡薄,现实的功利目的比较强烈——确保自己的土地、庄稼、房产、妻儿不受侵害。阿栋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吉丁村的民兵组织中,阿栋是个小领导,他虽然有点血性,内心尚有一点爱国意识,但自私自利,做任何事都喜欢权衡得失,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更不愿意冒风险牺牲,他趋炎附势也不团结其他战友,只在确保自己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完成可以讨好的工作,是一个聪明的投机主义者。同时,他还对读书人抱有敌意,认为他们又狡猾又有脾气,不值一提。游击战打响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撤退,在徐华峰需要他协助去解救被敌人围困的同伴时,他却自私地拒绝了。老实巴交的阿寿,本能性地恐惧战争,恐惧死亡。由于内心的空虚,阿寿始终处于无奈、被迫与惧怕之中。刚开始作战时,阿寿非常害怕,可不久就被战斗激发出了混合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大无畏气概,最后英勇牺牲。与阿栋、阿寿的写实性不同,阿劲、韦长松这两位民兵形象更具有象征意义。阿劲是民兵中的尖兵代表,沉着冷静,有勇有谋,爱国且个人英雄主义倾向浓烈;韦长松是吉丁村民兵组织与外来武装力量联系的桥梁,也是让吉丁村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破墙者,是属于德智兼备的民兵领导。虽然作家对阿劲与韦长松的刻画有待鲜明,但所传递的意蕴却明了清晰。
荣归军人是艾芜抗战小说中人物塑造上最具特色的一类形象。《重逢》中的潘雄辉是个可悲可叹的荣归军人,凭着运气没在战争中丧命,因得了一笔款子才有了底气。他没有荣归军人本该有的尊严和自律,反而因为有钱的打点马上投入到鲁德清为他安排的享乐中,没想到饭局中招来的陪酒女里,竟有自己的老婆芸香,他气急败坏,大打出手,最后统统被宪兵抓走,上演了一出让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潘雄辉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大家重逢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军人丢失了自己的气概,像个无耻流氓;抗属无人照顾,沦为娼妓,可悲可叹。《故乡》中的廖进伯,曾经一度带兵打仗,现在因事归乡,是一个有一定眼界和思想的荣归军人。所以他在“故乡”,既是一个实力派,也是部分青年的思想领袖。随着时间的推移,廖进伯的私欲和野心逐渐显露。他舍弃了军人的威严开始施展他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假装批评和关心各界问题,其实是在拉拢利益集团。他用他自以为是的处世之道,经营着他的归乡生活,试图掩盖着他的虚伪和狡诈。同样是荣归的军人,陈杰威(《故乡》)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一心想要上前线抗敌,却因为老母亲希望他回家生养后代而退出军队,终日卖酒为生十分痛苦。一个堂堂正正的抗日军人,在大敌当前时,却因为伦理关系的羁绊而放弃保家卫国的责任,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悲哀。
逃兵的形象以吴占魁和陈酉生最为典型。吴占魁(《田野的忧郁》)是个从部队跑回来的“兵大爷”,他什么也不怕,带着乡人去抢军饷。他既不因逃兵的身份而畏畏缩缩,不敢见光,也不怕打劫军饷丢掉性命,他怕的是割不到谷子,让依仗他的村民们活活饿死。可惜他不仅行动失败,还无力阻止梁大嫂和三个十多岁的孩子自杀而亡,自己还被密探追捕,变得进退维谷。靠一个还带有封建残余思想的个人的力量,显然无法改变广袤黑暗的乡村世界。陈酉生(《乡愁》)因受不了军队非人的生活而逃脱,但没料到回到家乡却又掉入另一个左右为难的“陷阱”。陈酉生曾说:“老实说,我就怕医好了又弄你去,叫你吃不饱,睡不好,苦得要命,到头还落得这一下场。你默倒我还怕打仗么?飞机坦克,大炮机关枪,这些人他们还见得少?他妈的,只要有想头,火里水里,狗养的才不敢去!”[3]13由此可见,军队不光对他们实施严重的虐待,还让他们彻底地失去希望。所谓的“想头”不仅指向物质报酬的匮乏,还可以理解为老百姓对内战的消极反对,对战争的疲倦与厌恶。八年抗战好不容易熬到头,谁又愿意再次卷入一场窝里斗呢。为了手足相残而拼命,许多老百姓都很难理解其逻辑基点,更何况,陈酉生早已被潜在的对手——共产党的“对穷人好的”品质所打动,决心冲出天罗地网后去投靠他们。艾芜对吴占魁和陈酉生的逃兵行为基本持褒奖态度,倾向于赋予他们一种耿直仗义的大无畏的梁山好汉的气魄,使这一形象有了新的特质。
艾芜笔下的难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迁徙的难民群,多是混乱无序地迁徙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荆棘上盲目来回的底层民众。《小家庭的风波》就是表现都市公务员阶层难民的代表作。屠先生因承担不起都市的生活花费而搬迁到乡村,可一再高涨的物价让他们的农村生活也变得困难起来,孩子们终日饥肠辘辘让屠太太下定决心像村妇一样开始卖小菜,可村里人认为屠先生明明有份体面的工作,太太居然卖小菜,完全是来挤他们的饭碗。生活的真相和城市人面子的冲突让屠家愁眉不展,坐如针毡。《都市的忧郁》中的袁大娘因为男人抗战牺牲,在农村无法过活便来到城市谋求生计,勤俭节约地攒钱只为能再回农村过自己原本的生活,但控制不住的物价飞涨让她希望幻灭,濒临死亡。《石青嫂子》中,地主吴大爷将内迁学校留给石青嫂子的田地“视如己出”,要求她缴纳土地交押金和租子,先是派人来威胁,后又派甲长来好言相劝,石青嫂子始终不从,最终一把火烧了她的家,石青嫂子只得拖着五个孩子离开家乡茫然地落难到城市中去。《一个女人的悲剧》中周四嫂子的命运与石青嫂子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石青嫂子的离开还带着坚毅和丁点希望,而周四嫂子还没来得及成为难民,就凄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胆小的汉子》中的张大哥被抓壮丁的威胁吓得举家逃到城市中来,改名易姓不说,还像逃逸的罪犯一般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心灵上的难民。这些无论是迁入农村的都市人,还是涌入都市的农村人,都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命线上挣扎,他们的迁徙就像被打散的蚂蚁们在盲然地寻觅着返巢的路,他们平凡而脆弱,不得不成为战火岁月中最深刻的体验者与最悲惨命运的承受者。
三、“回水沱”意象的典型书写
“‘洄水沱’系四川语汇,指江河中水流回旋形成的区域。在洄水沱,水流既平静徐缓,近于停滞,又深不可测,暗藏杀机,同时整条河道中的泥沙,污物又都汇积于此,‘内涵’丰厚。这样的停滞,阴暗和污浊似乎正是四川盆地落后、沉寂的象征,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便成了现代巴蜀生态的第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意象’。”[4]36这种表面上缓和平静,实则暗流汹涌,汇污积垢、杀机四伏且具有典型巴蜀文学气韵的“洄水沱”意象,在四川作家中较为普遍,在艾芜的抗战小说中也表现得相当典型。
在余峻廷的“故乡”,各界“名流”都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办实业、办教育、办报刊,实则为发国难财,满足一己私欲。教育局长徐松一与邮局局长陈洁林互相包庇,各取所需;地主土豪龙成恩与县长串通,霸占雷志恒家后山的官司势在必得;荣归军人廖进伯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八面玲珑,坐收渔翁之利。各方又因私欲膨胀而拉帮结派,暗中角斗。小学校长余峻城拉拢商界龙头蔡兴和,掀起挤兑风波,击碎徐松一的“实业”梦;优华中学校长周铭湘因办校款项与徐松一暗生芥蒂;龙成恩与廖进伯为办报之事产生不快。在前线社会状况动荡不安、水深火热,国人们或奋勇抗敌、或流离失所之时,大后方的“故乡”却依旧保持着麻木不仁的死水状态,且不是一个人的停滞和僵化,而是整个“故乡”小社会里,上至庙堂下至百姓的集体停滞与僵化。更可怕的是,“故乡”这个“洄水沱”不仅自身藏污纳垢,还形成淤泥沼泽使一些充满希望的抗日生力军深陷其中。雷庆生因钦佩当年驻扎过的红军老表的魄力,一心向往“故乡”以外的游击队生活,可怜哥哥雷吉生不但自己要逃兵役,还要听命于父亲,再三阻拦雷庆生的出走,害得雷庆生只能通过打猎来排遣打鬼子的心理冲动与愿望;雷志恒是有勇气和强力的印刷工人,从前线归来是为了“尽孝”,若不是执拗的雷老金倾家荡产与龙家打官司导致生活困窘,雷志恒早就奔赴前线英勇杀敌。但趟过“故乡”的浑水后,雷志恒更是驻足不前,直到因挤兑风波中父亲冤死而大闹衙门,才不得不像梁山好汉一般从“故乡”逃亡。余峻廷的家庭衣食无忧,但他一方面屈于母亲的淫威,一方面又乐于“故乡”安逸的乡绅生活,并幼稚地将抗日宣传计划的施行寄托在他人身上,几乎一事无成。在雷志恒深陷危难之际,还被廖进伯引诱一同游山玩水,将朋友的嘱托抛在脑后,最后若不是因为好友志恒、庆生的遭遇让他内疚并看清事实,余峻廷绝不会下定决心离开这块正在吞噬着他的“洄水沱”。
表面上看,《故乡》的直接取材地虽如作者所说在湖南宁远,但其所关涉的却是抗战语境下,中华民族大地上所有近似于“洄水沱”的地域。可以试想,这一地理位置上更靠近大前线的宁远尚且如此,那么,作者真正的“故乡”——偏安一隅的巴蜀之地的生存景观又将是如何呢?艾芜这样“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作家必然会痛感于故乡的压抑和停滞”[4]46,特别是当他几乎出于责任感地试图掀开心灵的重压时,必然会选择透视自己最熟悉的家乡,通过“洄水沱”的意象来释放心灵的重压。这也是《故乡》立意所彰显的巴蜀气韵。
如果说《故乡》的“洄水沱”意象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整体状态的象征,那么《山野》当中的“洄水沱”更多的体现在个体人物身上。“故乡”小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提供了其成为一潭“死水”的客观条件,然而,位居于南方“山野”的吉丁村就没有“故乡”那么幸运了。故事开始时,整个吉丁村就已经陷入战时状态,时刻防范着日本人的进犯。乍看上去,似乎整村的男女老少都意识到了只有抵抗才会获得争取自由的真正机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村中最富有的地主韦茂廷有着丰厚的还未被掠夺的家产,逃难到亲家的徐德利称日本人的侵略为“劫数”。因此,韦茂廷希望投和保全家产的愿望与徐德利的亡国论不谋而合。他俩一同找村长兼抗日作战总指挥韦茂和商量投降事宜,被韦茂和拒绝。因为茂和在镇上的织布厂、染房、米店、房产都在前次日本人进犯时化为了炮灰,出于为自己化为泡影的产业复仇的缘故,他开始组织村人进行武装反抗。他大女儿韦美玉说:
他只踏踏实实做有利的事情,他不喜欢哪个拿大帽子给他戴的。你默倒,他如今打仗,是为了想得爱国那些好名声么?全不是的,一点也不是的!他只为了他的财产和地位,他从几十亩田挣到了几十万家私,他从摸锄头的种田佬爬到了镇里大商家,人家一下把他干光了,想想吧,他会甘心么。……[2]143
也就是说,茂和之所以一开始拒绝议和坚持反抗,只是因为咽不下财产散尽的那口气,支撑他的动力只有复仇。所以当战况急转直下,韦茂和发现不仅不能复仇,反倒性命堪忧时,他唯一的动力消失了。这时,韦茂廷早已逃之夭夭,徐德利又来吹耳边风,韦茂和不仅同意了议和,还企图让韦茂廷经手,好为自己事后推脱责任留后路。作为抗敌领头人的心理觉醒程度尚且如此,那些直接面对刺刀机枪的村民们的内心可见一斑。阿栋参加抗战首先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产业,再是不愿他人瞧不起自己。同辈的阿寿代表了更为普遍的心理,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不得不战,内心的空虚又使其无法获得战斗的勇气和动力。从村长韦茂和到村兵阿寿,他们或是干脆逃跑、或是倡导投降、或是被动抗战,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了小农意识和实用心理所造成的痼疾。他们表面都不动声色,但内心各自敲着肮脏、自私又冷血的小算盘。对当前的局势认识混沌,对自我的觉醒毫无意识,遑论爱国或爱民族。哪怕大敌当前,在乎的也只是自己埋头看见的巴掌大的利益。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与“洄水沱”所象征的停滞落后、封建腐朽如出一辙。
如果说,自私麻木者常常打起自己的小算盘,那么,那些有着爱国、抗敌自觉意识的人物又会如何呢?知识分子代表徐华峰一向主张坚决抗日,大力宣传并鼓动阿岩、阿龙、阿劲投身战场,但妻子韦美玉一心扑在保全自己的小家庭上,不断劝说其放弃吉丁村逃往大后方,不惜利用徐内心的软肋(在战争状态下,文人没有用武之地)来刺激他,引发出自己内心的自卑感,发出“可惜自己不是一个武人”[2]146的感慨。这一心理顾虑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总想在村民面前做一个思想的领导者,却又始终自认在“武人”面前说不起话,连想救深陷敌人包围圈的同伴的想法,最后也演变成“让我下去!我就要下去给他看!”[2]325的证明行为。在外人眼中,韦美珍绝对是以大胆泼辣、倔强不驯著称的,但内心依然乌云密布。她惧怕未知的战争,她去为驻守前线的伤员看病,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逞能、好强之举。所以,当她听到沿途村民的不理解声,看到煤矿队战士的油滑和冷漠时,她收获的全是灰心和失望。就连抗敌英勇的阿岩、阿龙也有“二心”,想要离开吉丁村,投靠长松的挖煤队,“那样一心一意地打仗,活得痛快些,省得在这里,命拼了,还要看他们的嘴脸。受他们的气!”[2]212-213而阿龙劝说阿岩之所以还不能放弃村子,不是因为至亲、故里的关系,而是“我们留着村子,我们是要留着粮食呀!”“我们就得要使他们高兴给呀!”[2]214由此可见,徐华峰和美珍虽有自觉的爱国意识,但对抗战和自己的认识和定位还不够清晰,加之性格的因素,不时涌出隐藏在积极抗日表象下的内心漩涡。而作为阿岩、阿龙这一类只管拼真刀真枪的战士,其自觉意识也不够强大,他们靠的是天生的血性和野性,和隐蔽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那种因为历来贫贱而希望通过拼命保卫村庄得到尊重,获得农田和地位的单纯愿望。当他们发觉期望在很大程度上会落空时,内心掀起了愤怒的波澜。这一类人都是暴力反抗敌人的支持者,但内心都有着或大或小的泥沼,让他们不时迷糊了双眼,就像“洄水沱”一样,表面看似平静,其中却暗藏矛盾与危机。正是艾芜清晰地以“洄水沱”意象揭示了巴蜀人内心的隐秘与复杂,揭示了抗战时期乡镇底层民众的社会心理,才使《山野》的人物与立意呈现出鲜明的巴蜀文化气韵,焕发出动人的艺术魅力。
总之,艾芜的抗战小说具有浓郁的巴蜀文化气韵。如《山野》在艺术手法上,作家或通过叙述者对叙述手法与叙述时间的控制,即通过插入停顿、重复叙述、倒述等手段,改变文本的叙述时长,形成缓慢匀缓的速度与节奏,契合巴蜀之人安逸闲适与自由散漫的性情,或以简单的几个人物勾画出一场耿直燥辣、爱恨分明,充满激情的山地战,映现巴蜀儿女耿直燥辣、爱拼敢闯的人物性格。在人物塑造上,艾芜以蜀地民兵、荣归军人、逃兵以及难民等,组构成其抗战小说的人物全图,其中,又以荣归军人塑造最具特色。在小说意象的营建上,作家以具有典型巴蜀文学气韵的“洄水沱”意象,将表面上缓和平静,实则暗流汹涌,汇污积垢、杀机四伏的巴蜀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艾芜的抗战小说呈现出特有的巴蜀文化气韵,焕发出动人的艺术魅力。
[参 考 文 献]
[1] 李怡,肖伟胜.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M].成都:巴蜀书社,2006.
[2] 艾芜.山野[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
[3] 艾芜.乡愁[M].上海:上海中兴出版,1948.
[4] 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The Elements of Ba-Shu Culture in Ai Wu' s Counter-Japanese War Fictions
Chen Siguang Liu Di
(School of Literature &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DX Jointly Publishing House, Shenghuo Publishing Co Ltd, Beijing100010, China)
Abstract:Ai Wu' s Counter-Japanese War fictions are featured by elements of Ba-Shu Culture. When it comes to artistic techniques, he changed the narrative duration through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narrative time in the control of narrators, namely narrative interspersed with flashbacks, repetitive narrative, flashback narrative, etc. All this forms a slow and gentle pace, which conforms to hedonistic and free temper of people in Ba-Shu areas . On the other hand, he portrayed a fierce battle in the mountains, which demonstrated the uprightness and courage of people in Ba-Shu areas. In terms of character developing, Sichuan soldiers, honorable veterans, lamasters, refugees and others constitute the character panorama of Counter-Japanese War fictions, in which the honorable veterans are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s. When it comes to images in his fictions, Ai Wu chose "Huishuituo", the most typical image with Ba-Shu literature elements, portraying the superficially tranquil but actually dangerous Ba-Shu features in detail. All this gives Ai Wu' s Counter-Japanese War fictions unique elements of Ba-Shu Culture.
Keywords:Ai Wu; counter-Japanese War fictions; elements of Ba-Shu culture
收稿日期:2019-09-06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思广(1964—),男,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刘笛(1988—),女,文学硕士,北京三联书店编辑。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16ZDA191);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17BZW153)。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5-0022-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503
来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5期 P2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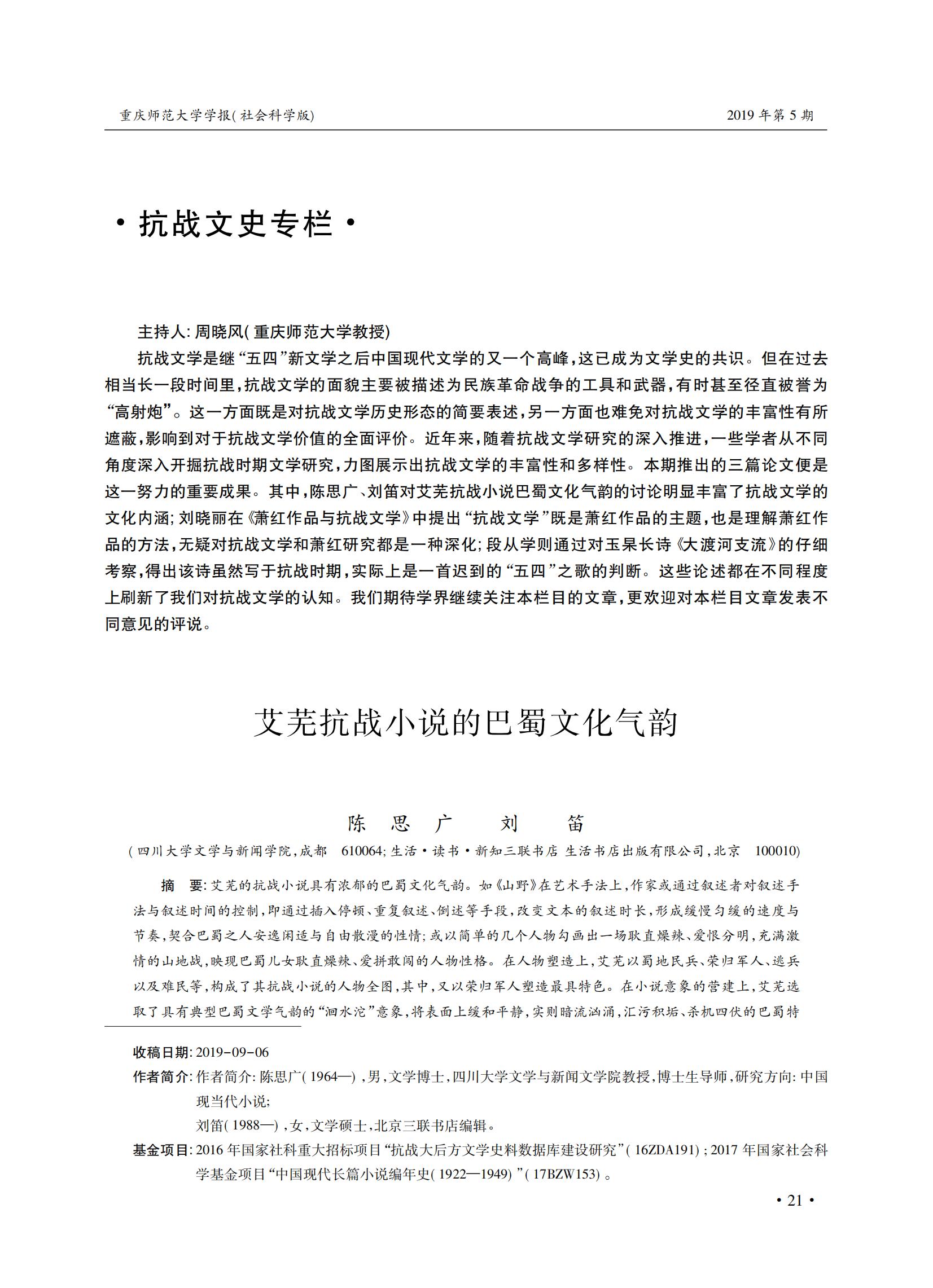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24 10:23:46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战时经验与孙犁抗战小说的美学创造
下一篇:论路翎抗战小说的英雄书写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