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尔劫掠者突击队员在缅甸
2020-02-25 09:13:25 来源:中国远征军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翻译:戈叔亚
译者注:这篇文章是以一个在第一线作战的老兵的亲身经历的回忆录,这个老兵才是真正在第一线面对面和日本鬼子作战的老兵,他的回忆录太有感性认识了,如同您亲临其境,让读者感觉可以感觉到了原始森林的水蛭爬在你的大腿上吸食你血液的一股异样的清凉感,可以闻到腐尸、泥土、硝烟和树叶甚至烤肉的混合气味、感觉累垮前眼前跳动的景象的不真实感……总之写出了第一线的大兵最真实的感受。这样的文章实际上您在接触老兵时,几乎是完全找不到的,原因很多很多:更多的老兵没有接触血腥的战斗,而接触过的你又很难找到,他们都是最底层的士兵,这样的士兵都是在偏僻的农村老家;他们没有文化,无法表达最触及灵魂的,最可怕的部分;等我们找到这些老兵实在是太晚了,他们的这部分神经已经麻木了死亡了……他们接受过一点错误的表达自己在战场的思想感觉的模式,这些模式是最糟糕的……
像这样的文章,不是随时随刻可以遇到的,现在,我遇到了……
袖手旁观的评论家们对梅里尔劫掠者有很多要说的话,但评论家远离了无路可走的丛林,再找这些地方,除了劫掠者突击队员的英勇事迹,什么也没有留下。下面是一个在场的人(弗雷德·莱昂斯上尉)讲述的故事:
这条滇缅公路是中国著名的生命线,外界对我们行军和战斗的结果相当熟悉,缅甸地图证明了这一点。人们知道,我们只有三千人起家,只有三个营,并不是所有的三千人都回来了。但自从我们回来后,人们对梅里尔的劫掠者提出了许多问题。他们都说我们解散了,崩溃了;我们的士气被粉碎了,尽管我们赢得了胜利。说这些话的人不知道我们的故事,因为这是我们在千里之外留下的脚印,在那些没有人迹的群山河丛林中留下足迹,在那些有着吸血的水蛭和吼叫的狒狒、雷鸣般的大象和沉默的日本人的丛林中留下足迹。是的,在那里可以找到关于梅里尔劫掠者突击队员所有问题的答案。嗯,这是关于那些脚印穿过漫长而可怕的缅甸的故事。我记得就说出来,就像从一开始就发生在我身上一样。
1、部队组建,秘密集结、训练
我在特立尼达驻扎了将近两年,我开始感觉到战争正从我身边掠过时,1943年8月的一天,我的团长H·麦基上校(H.McGee)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你想在一个活跃的战区里自愿参加一个危险而刺激的秘密任务吗?”他问我。一个危险而刺激的秘密任务!我的心跳了起来。这不是我一直在等待的吗?
当然可以,”我回答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发?”麦基上校问了全团所有官兵同样的问题,每个人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但最后只有1100人被允许去。我感到很幸运,因为他们带走了我。从那时起,一切都变快了。每一架非洲航线上的西行运输机都被指定在特立尼达降落然后被扣留。等待预订数周的乘客被迫再等一段时间,士兵们一批接着一批上了飞机。最后轮到我了,我登上了一条巨大的飞机,开始了一段漫长旅程的第一站,第一站在迈阿密海滩结束了。
在那里,我们守口如瓶。我和那些人一起被限制在一家旅馆里,甚至不允许我在街区走动或打电话给我200英里外的家打电话。其他自愿参加“危险和刺激的秘密任务”的人也涌入其他旅馆:来自牙买加的骑兵、来自波多黎各的工程师、来自巴拿马的步枪手、来自华盛顿的无线电专家。他们没有比我更多的找到关于我们要去哪里或我们要做什么的信息。
第二天早上,我们登上了两列拉着窗帘的火车。五天后我们到达了旧金山。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去欧洲。在加利福尼亚州匹兹堡的军营里,我们被注射了预防热带或北极气候疾病的疫苗。我们以为我们买羊毛衣服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第二天我们又得到了一套棉质制服。谣言工厂被投入生产,四处散步他们的产品,但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最后,就在开航之前,我被允许打了一个电话。我在佛罗里达州打电话给我母亲,但我只能告诉她我暂时不会见到她,也不用担心。她说:“好吧,儿子,照顾好自己。”如果她相信奖牌的话,我会给她一枚。在一艘改装过的豪华班轮上,我发现我们将为我们神秘的使命接受大量的训练。日复一日,我们在宽阔的甲板上跳下,蹲下,用刺刀格斗,用枪托挡住。我们对着摇摇欲坠的日本军官士兵的硬纸板脸开枪,对着日本坦克和飞机的纸板模型扫射。
我们必须学习很多关于与日本人战斗的知识,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在新喀里多尼亚,我们遇到了来自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脸上的皮就如同皮革外套那样粗糙的老兵。在船上,退伍军人被分配到我们部队中的位置,以便给我们的新手增加份量和经验。那时,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南太平洋。在其他港口,我们只在几个港口上岸几个小时。几年来最受欢迎的景象是见到印度大陆,因为这意味着漫长的海上航行结束了。
2、在印度集结——印度阿萨姆邦雷多(Ledo)小镇
一列嗡嗡作响的火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休养营,三周后我们搬到训练营。在那里我们第一次了解到我们的战场将在哪里。是现实传说中的“剑与圣经”温盖特将军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他把他前年在缅甸的著名突袭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的经历中获益,活着走出丛林。我现在看到他了,他那像鹰一样的脸活跃起来,因为他警告我们,不要在丛林里低声低语,不要试图拔掉吸血的水蛭,不要喝丛林里的水而不消毒。两个月来,我们在丛林的演习中训练。我们被分配到丛林服装,不是新几内亚男孩的斑驳迷彩制服,而是坚实的深绿色服装,在丛林中提供了更完整的隐蔽性。我们抗疲劳的上衣和裤子,我们的衬衫和内裤,甚至我们的手帕和火柴都是绿色的。我们日日夜夜地前进,奔跑,躲藏,装模作样,又一次地学到了美国先锋队在同印地安人的斗争中第一次学到的东西。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准将(现在是少将)弗兰克·梅里尔,也在学习。我们变得像绿盔一样坚硬,像我们美国兵绿色军鞋一样坚韧。我重146磅,身上没有一盎司的脂肪。我可以跑20英里,还能在一个印度村庄凉爽的夜空中轻快地散步。

劫掠者部队的总指挥 弗兰克·梅里尔(Flank Merrill) (左)和史迪威在一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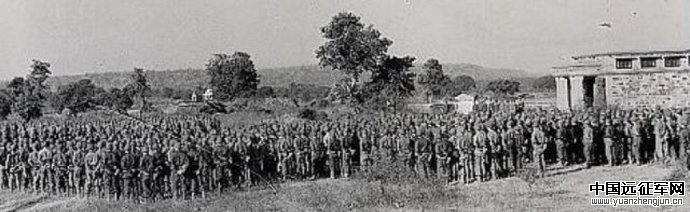
5307混合部队(临时)就在1944年2月离开印度阿萨姆的雷多之前。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一列摇晃的、滚动的火车把我们载到离缅甸边界附近大约8英里的一个小镇雷多。补给品在等着我们;骡子和马正在有栅栏的田野里奔跑;在简易的飞机跑道上准备运送补给物资。1944年2月7日黄昏时分,人们和动物们纷纷排成一队,沿着雷多公路前进,这是一片40英尺宽的崎岖土地,从印度一直延伸到缅甸,并与日本切断的著名滇缅公路相连。这就是这次行军的原因:日本希望切断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联系,这条生命线可以把源源不断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被围困的中国,最后这条路线变成一股洪流。在我所能看到的前方,是那些戴着绿色头盔的人摇摇晃晃的脑袋,他们的背上骑着绿色的背包。骡子们一路奔驰着,他们的背包随着行军的脚以有节奏的动作从一边向另一边摇晃。在缅甸的月光下,白茫茫的脸庞在我身后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消失。谈话一波三折。匹兹堡中士索科洛夫斯基(Sokolowsky)说:“我希望这件事很快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不会是一次短途旅行。”但有十个晚上,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的感受。所有的东西都在行进。天亮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公路,在丛林中扎营,直到日落。137英里的时间里,我们只被100辆卡车车队的尘土惊扰,他们正呼啸而过,为中国军队攻击缅甸北部的日军提供了条件,透过错综复杂的藤蔓、榕树和青草的光线,还不足以让两英尺远的地方看到一棵树。
每个人都把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的信息传给身后的那个人。来自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的“医生”亨利·斯泰林(Henry Stling)会向我靠拢。过了一会儿,我会站到高处,以避免一根咬人的榕树根伸过小径。我靠近科洛斯基,然后低声低语,然后把话一个传一个,传到了队伍的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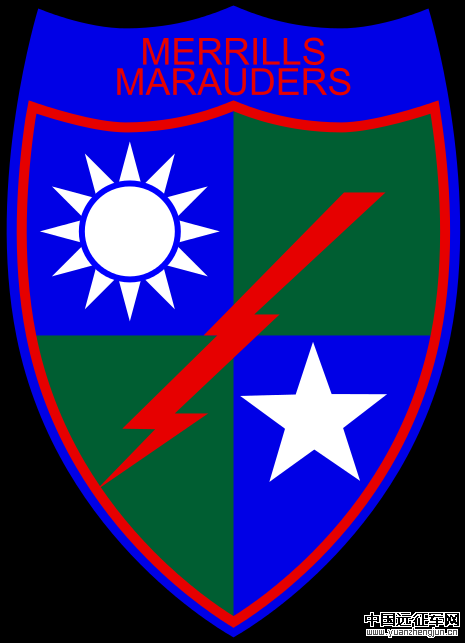
译者注:这是美国梅里美劫掠者(Merrill's Maruders)的队标,和火神(火星)的队标一样。注意看,里面有一个中国军队的标志,说明这支部队曾和中国军队是肩并肩作战的。据说现在美军特种部队的标志都是这样,我认为是可能是。他们都有一个尊重传统的习惯。
3、秘密进入缅甸,缅北胡康谷底(野人山)
然后我们来到了雷多公路的尽头。我们在丛林中开辟出了一条三英尺宽的小径,白天行军,因为我们晚上几乎不能在丛林中行走。尽管月亮是明亮的,但透过蔓生的藤蔓、榕树和青翠的光,也不足以让一棵树在两英尺之外可见。
我们正靠近胡康谷地的顶端,我们知道日本军队会在那里。偶尔会有一群叽叽喳喳的猴子的声音,被我们的接近吓到了,开始跳过树林,我会听到它们在远处发出的尖叫声。“该死的那些猴子!”索科洛夫斯基不止一次地说。“它们会把我们在这里的秘密告诉日本人。”有时我们低声交谈,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默默地行进,沿着缅甸土著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的蜿蜒的小径,一次数英里,我只想一件事,比如一碗意大利面。当我们走到山谷时,我们打包的食物就已经装好了。我们一起跑出去了,我们要求空投。第一次空投补给品是一次相当大的经历。我派人照看部队的物资,然后爬上岩石去看。就在预定的两点钟,飞机轰隆隆地飞过来,上下飞来,好像在扫树梢。然后从他们的大肚子里滚出箱子、包裹、箱子和袋子。箱子像提线木偶一样在降落伞弦上晃动,但骡马的饲料袋却像迫击炮的声音一样轰然落地。经过两天的休息,补给品被分类和分配后,我们又开始了一次行军。
我们在爬山、爬山,似乎攀爬喜马拉雅山南麓,以避开山谷里的日本人,越过他们的防线。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起来。我们每小时只能爬上一两英里,然后我们就经常有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危险,从200英尺的高空跌落下来。 大部分的小径都建在山脊上,两边只有峡谷。晚上,我们进入了我们的轮式营地,中间有马匹物、重炮和其他装备,机关枪和炮手形成了圆形的边框。每天晚上,我们都离日本区更近一点。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山谷。根据我们的侦察兵和史迪威将军总部的消息,我们已经超过了日本人,我们现在准备向他们的后方进军。
4、第一次与日军交战
梅里尔将军在一次参谋会议上解释说,我们将堵住道路,以阻止日本日军物资向北流动,并尽可能地保持下去,然后撤离。麦基上校挑选的地点位于瓦鲁班(Walawbum)附近公路的低处,那里发现了一处日本人的营地。我派了一支巡逻队去察看这个地方,36小时后,我们沿着那条小径走了进去。我们走进山谷,离开了乱糟糟的丛林,穿过像甘蔗一样摇曳的象草海,高耸在头顶上。前面的人拿棍子边打边走,用廓尔喀族人(Gurkha)刀砍杂草,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发出太大的响声,并在途中引起涟漪。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行动,我很害怕。当我沿着摇曳的草地走着的时候,我想到了所有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我想我该如何在路边架设迫击炮,准备把炮弹倾泻到日本人的炮阵地上,怎么把机枪组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打过来。当暮色降临到夜色中时,我们走到了一英里之内,靠着熟悉的马驮车轮过夜。
上校派我去检查边界线。当我小心翼翼地穿过象草地的时候,我能听到日本人在远处的笑声和喊叫。我想他们是为了驱赶我们的另一个营而去的,因为如果他们以为我们在附近,他们肯定不会被听到的。这让我有点发冷,但我摆脱了这种感觉,重新考虑了攻击的布局。它将在黎明开始,所以我决定睡个小觉。我让一个站岗的人在五点叫醒我,然后躺在地上,头放在背包上打瞌睡。我不需要第二次叫醒我。卫兵推我的时候我马上就警觉起来。在黎明前寂静的黑暗中,这些人悄悄地走来走去,准备好他们的背包,他们的弹药装好了,他们的刺刀上好了,汤姆逊枪上膛了。我们沿着小径前进。慢慢地,我们到达了路边的低谷。然后让我惊讶的是,一名侦察兵在对讲机上叫了回来,“他们正在撤离。”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设置路障,没有开一枪。
日军在夜间向我们在瓦鲁班的另一个营发动进攻,他们的散兵坑前面很开阔,我们开始把散兵坑挖得更深,这样两个人可以同时占领一个。与此同时,炮手们正在收拾残局,迫击炮手们正在把他们的三块外加药放在一起。我四处走动,看看交叉火力是否覆盖了所有的通道,当我们发现留下散兵坑的部队回来的时候,枪炮正在开火。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蹲在散兵坑里。我能感觉到我的肌肉在抽搐,血液在我的脸上砰砰作响,我小心翼翼地移动我的位置,在路上窥视着。“就是这样!”我想。然后,从一片缅甸平原的寂静中,突然传来一声机关枪的嗡嗡声。它吓了我一跳,激怒了我旁边的卡达莫( Cadamo )中士。他跳到下一个洞去抓住炮手的肩膀。“你在干什么?”他沙哑地低声问道。“你想什么?”炮手顶了一句,指着路。卡达莫摇摇头,又回来了。我很兴奋。“那个傻孩子做了什么?”我问。
“见鬼,他让七个日本鬼子一排排地沿着马路走来,然后全部干掉了,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连发。”接着,射击开始了。更多的日本人跑了进来,离得太近了,你可以看到一颗青铜星在他们小帽子上黯然失色地闪光。托米枪停下来只是为了一个接一个地换上子弹,日本人躲开了,融化在草地里。肯定杀了一百人,但一切都匆匆结束了。我们了解到,整个日本第十八师团都要回到山谷里去,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向山坡走去。我们第一次封锁道路的时候做得还不错。我们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余脉休息了两天,在那里我们用降落伞重新装备了补给,然后我们又开始了徒步旅行。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一半。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往上爬。有一条山脊太陡了,我们不得不在岩石里砍出凹槽,用吊索来支撑自己。我派人在下面的凹槽上抬骡马,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几匹马在下面的峡谷里摔死了。到了一个峡谷里,我们发现了我们迄今为止最困难的地形,这是一条不超过腰部深的河。我们会紧紧地抓住一条河的河岸,然后发现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行走,我们会涉水穿过另一边。我会踏进一个小洞,几乎沉到腋窝,抓住一头骡子的尾巴,不让它沉下去,然后把我的鞋上的淤泥和鹅卵石都蹭空了,然后继续前行。我们来回地涉水,直到我昏昏欲睡,我甚至没有想过我们穿过的次数。但是当我们接近20英里的河流尽头时,索科洛斯基说话了:“你知道我们穿过这东西多少次了吗?”大约30次,我想,“我呻吟道。“见鬼,”他说,“我一直数着。现在是趟过的第49次河流!”我们过河49次,只是为了跑20英里。就在日本路附近,我们计划设置第二个路障,我们小心翼翼地、安静地走着。又一次出现了紧张的紧张期待感。然后命令又回到了那条线上:“点开火,点开火。”
我伸手把挂在信号机包上的无线电话从钩子上拿了下来。“怎么了?”我问。但无线电里面太忙了。营部发出命令,要列队展开,纵队正分头离开。最后我知道了发生了什么。这个重要的人,小队的头,遇到了四个骑着大象的日本人。他们杀了三个,但一只逃跑了。现在我们知道日本人会发现我们。我们在我们的货车后藏好,挖好躲藏的洞,为即将到来的刮痕挖洞。我们知道日本人要来了,因为我们在路上整夜都能听到卡车的轰鸣声和砰砰的一声。每一次撞击都意味着另一卡车日本士兵在卸货。
早先的时候,我听说过日本兵毛骨悚然的自杀冲锋,现在我正站在这样的冲锋的中间。我正从灌木丛里抓着枪柱时,看到了第一波自杀冲锋。他们是六英尺高的日本大兵,穿着黄色的卡其布制服,就像麻袋一样包裹着他们。日本人的脸上没有多少表情,但我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四周的紧张,当我们的机关枪击中时,他们的表情变成了震惊和惊讶。一个日本人的步枪在他倒下的时候似乎像长矛一样飞起来。另一个日本人的步枪掉在地上,正好刺到了自己的肚子。我爬向四周,进入了一个新的散兵坑。沿着斜坡,我看到了一场奇怪的致命搏斗场面。
一个日本人和一个名叫赖安(Ryan)的男孩跳进了一个散兵坑。赖安抓起了日本人的步枪,他们扭打、拉扯、扭伤对方的手。没有人胆敢向日本人开枪,以免伤到赖安。突然发生了这件事。终于瑞安的枪响了,日本人软绵绵地倒了下来。赖安摔开日本人胳膊跳了起来,躲开了路。他从日本人手臂上跳起来,跳上前去。当他跳下去的时候,一梭机枪子弹打中了他。第四波冲锋失败后,日本人的尸体堆得那么深,在战斗中的一段时间里,卡达莫(Cadamo )不得不溜出去,拉开上面的尸体,以便清除射程,保证射击顺畅。在另一支枪面前,我数到了七具尸体。最后,等待了几个小时,没有更多的日本人爬上那片血腥的山坡。当人们跌跌撞撞地走进他们的巢穴时,大家非常紧张。战斗结束了。还没来得及重新开始,我们就向喜马拉雅山南麓进发,在那片死亡和痛苦之地的上空6000英尺处,我们以威严的姿态出现。当夜幕降临时,我们又在岩石峭壁上又一次了解到,日本的主力又从史迪威的中国人的强攻和我们不断的从后方打击退回来了。

1944年4月,在Naubum第一营的军官们,这是在前往密支那之前。
5、成为了老兵,常常摸到日军屁股后面堵截他们的后路——Nhpum Ga村子的战斗
无数个山间露营的夜晚,更多的沿着山脊跋涉的日子。我们离开雷多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但仍然看不到尽头。当我们的营到达Nhpum Ga(那加人的村子)时,我们正走向空投补给的场地。这个山脊几乎预示着三分之一梅里美劫掠者突击队员的厄运。日本人在那座山上堵截住了我们,切断了我们和其他掠夺者的联系。我们有1100人被困住了。鬼鬼祟祟、爬行的日本鬼子做得也不是那么好,因为我们终于也发现他们了,他们的迫击炮向我们一个劲地打来,使得我们的人员和马匹,补给品都有大量的损失。没有一条小溪,我们很快就需要水。 四周没有溪流,我们感觉口渴的厉害。我们寻找周围的竹子,用到劈开竹子,喝里面的水。但是竹子里面的水,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一千人的需要。森林小径的大象的脚印里有一些水,我试着把浮渣撇掉,俯下身子,把屁股翘得高高的,喝这里的水。虽然我把消毒药品放到水里,有股白垩的味道非常恶心,试着用柠檬水药片处理它,甚至尝试用这样的水煮咖啡和奶粉!它的味道仍然和湿泥一样。回到雷多基地,他们回复我们的无线电请求,派飞机送来补给品,第一次降落伞里是装有铝制螺丝头的塑料桶。当我看到那些装有香肠-像瓶子一样东西从降落伞上飘下来时,我发出了热烈的感谢祈祷。我们终于喝了水!
我们日日夜夜受到攻击。每个人必须时刻和自己的枪呆在一起。我从雷多基地叫来香烟,这是第二次空投带来的大量的香烟。烟壳上几乎没有品牌,上面写着它们是由美国军团和公民俱乐部捐赠的。在由于紧张和疲惫,突然让男人们的眼睛闪烁着希望。

劫掠者队员在瓦鲁班以西前往密支那之前的路上合影
6、尸山血海的战斗
他们开始叫这座山脊为“蛆山”,因为到处是马的尸体,战壕里是死掉的日本人的尸体,腐烂肉体的臭味变得越来越强烈。炮弹轰击而入,我们只好把这些尸体拉出战壕,因为我们需要使用战壕躲避炮弹。
在一次空投补给中,我们预定得到手榴弹。降落伞落得很分散,很快我们自己的手榴弹就开始在我们头上爆炸。日军狙击手爬进了我们头顶上的树上。当我在铺设一条电话线,一颗子弹打在我脚外几码远的地方,溅起泥土。我扑通一声卧倒,四处张望,但什么也看不见。 又有一股刺鼻的硝烟扬起一点泥土迎面飘了过来。我扭动着,用力拉着我的电线。又是一个扬起泥土的冒烟。原来是是一个日军狙击手,躲在茂密的树丛中的一棵树上,朝我开枪,五次都没打中。
一个营的日军正试图穿过峡谷冲向我们,他们也不停地遭受损失。听到我们的困境,雷多后方部队的厨师整晚熬夜给我们弄点特别的东西。我们真是受够了单一口粮,我们靠咖啡和香烟生活了八天。接着,一盒又一箱的油炸鸡,在白色的大褶皱下飘浮下来。战斗还在进行,距离300码,看到一个离奇的场面,一群穿美军作战服的人相互拍打胸部和大腿。他们高兴地吃鸡。
正当这场盛宴正向后面的士兵延续展开的时候,日本炮火开始了,男孩们散开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回来的人发现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再尝一口那些鸡,因为没有剩下的了。日子过得太慢了。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因为病得站不起来,只能躺在箱子和包装袋上。医护人员冲来跑去照顾伤员,为死者挖了浅坟。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好像几个小时,就像几个星期。实际上,中国军队的救援物资在4月9日空投以后才过了15天。我记得那个日子是因为有人说是复活节星期天。那天,我们从山上飞了下来。我们的马匹所剩无几们,从原来的400匹,现在只有89匹了。我们在返回的路上到一个新的地方休息。不过,在伤员被疏散之前,我们不得不建造另一条空中跑道。缅甸稻田的小泥挡土墙被推倒,磨平了,一端的树木被砍掉,另一端的土质堤岸也被挖断,这样我们才有勉强的跑道,可以供小小的蚱蜢飞机(可能是指L-2小型观察机,仅仅能能乘坐两人)的起飞。它们那矮小的马达发出的嗡嗡声对病人来说是美妙的音乐,然后一个接一个地飞回医院。
虽然在旅途的两个月里,我一直保持着体力,但我需要越来越多的努力才能继续前进。我患有阿米巴痢疾。当我从大象的足迹里喝水时,医务人员认为我感染了痢疾。因为除阿米巴之外,哈拉酮药品能杀死所有细菌。
7、深入敌后长途奔袭,秘密接近密支那机场
然后,我也流失了了大量的血,是被水蛭(也就是蚂蝗)偷吸的,那些可怕的灰褐色寄生虫,把头埋在你的血管里,吸到比正常的蚂蝗个头大几倍的血。我学会了如何通过用燃烧的香烟烫、碘或盐来清除水蛭,但它们总是在我的毛毯下被发现。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要做一次检查,看看有多少水蛭在我的身体里度过了一夜。有一次,有九只水蛭和我在一起,它们吸食我的血,膨胀到半条香肠那么大。有些水蛭居然跑到了一些男孩的耳朵和鼻子里,然后医护人员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技术。似乎水蛭入侵我们的事件在下降。似乎一只水蛭喜欢伸下来把尾巴放进附近的水里,所以医生会在水蛭患者的鼻子或耳朵下面装一杯水。当水蛭伸下来时,医生会用绳子拴在尾巴上,拉紧。然后会把一根燃烧着的香烟的末端碰在水蛭上,它马上就会松脱。但是如果你只想把它拔出来,它的头就会在你的皮肤下面脱落,断为两节,一节深入你的皮肤下面,引起感染。
其他的疾病也在劫掠者突击队中间中间爆发:黄疸、疟疾、胃病……但我们一直坚持着。我们的目标是密支那,我们不愿在到达之前放弃。当我们从战线撤退下休息,休息结束时,我们回到山地,开始我们的最后一次驾车行军时。那时候,我似乎不能再坚持一天了。当我们到达一座山的顶峰,也许是一英里高的时候,我们会往下看,在下面一英里处,看到另一座山谷,另一座山在北边。也许下一座山的峰顶距离我们只有半英里远,但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我们还有两英里的路要走。
开车,开车向前,我们一点地爬上另一座山。爬上去,我头上的血液因拉藤蔓和拉骡子而在我的头上鼓起。往下走,我的脚后跟差不多要跳到我的脊背上,每走一步都像是打开了一口伤口。我什么都想不起来,除了“我们必须要做的事,不可能有太多的事了。”还有更多的路要走。“然后又来了一座小山。
有时我会看着亨利·斯泰林医生,他背着的包是其他人的两倍,我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怎么做到的。然后医生展示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在补给品投放时,他的医疗用品被夹在一棵树顶上,上面挂着降落伞。它一定有50英尺高。这次空投的是我们两天所能得到的所有补给。医生找到了一根绳子,固定在一棵树上闪闪发光。从下面我们看到当他终于到达降落伞,解开帆布袋时,一阵响亮的欢呼声响起,附近没有日本人,医生挥手笑着,然后开始下降。他保存了宝贵的补给品,可能是这样。那次攀登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
不知怎么的,我们从山上下来,靠近密支那。我们再一次驾起马车,派巡逻队去接触一下日本人。我们很快就接触到了。其他几个营从不同的路线上走了过来,很快我们又陷入了狙击和战斗的泥潭。
我在铁路沿线带着一个巡逻队。到现在为止,我的痢疾已经非常厉害,已经开始流血了。每个人都因某种原因而生病。我的肩胛带被磨损了,我背着背包,只带着步枪、弹药和皮带。和我在一起的男孩状态也非常不好,但是我们沿着铁路向上移动,在轨道附近安放着一把汤米枪。一个侦察兵向前走,突然把步枪高高地举在空中。这意味着“发现敌人”,然后他开始移动步枪上下左右。这意味着“向敌人射击”。
我们弯腰回到灌木丛里去看。我对结果几乎无动于衷。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他们,沿着铁路一路走来。
8、突袭占领机场,我们彻底累垮了
日本鬼子根本不知道我们在附近。枪手拿着枪蹲着,收紧了身子。然后开枪,击倒了5-6个日本人,然后又打倒了5-6个。前进的纵队从行军纵队列马上钻入灌木丛里。我们拿起枪,滑回丛林里。有时摇摇晃晃,有时跑,有时拖着,我回到了营地。我病得很重。我不在乎日本人是否突破了,我再也不担心让上校失望了,我只想失去知觉。
“伙计们,我得把这次行军称为旅行。”我告诉医生们。他们看着我,说他们猜我是对的。所以,我躺下,等飞机来把我送回雷多。我是最后一批离开密支那的劫掠者之一。我离开是因为无论我多么想继续战斗下去,我都不能再走了。我病了,精疲力竭,身心都垮了。我知道其他人也是这样。劫掠者的瓦解不是由任何一个原因造成的。在行军的整个过程中,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不,他们没有退出;他们是掉了下去。起初是意外伤亡,在山脊上摔断腿的人;肋骨被托炮的骡马踢伤。在设置第一路障后,疾病开始造成死亡。在第二个路障设置之后,Nhpm Ga战斗结束后,空中撤离的必要性随着战斗创伤和疾病的发展变得更加急迫。 当我们完成每项工作时,看起来好像我们会有所缓解; 但是马上我们就有另外一份工作要做。密支那机场的战斗把本已受伤生病劫掠者队员弄得极度疲劳。 我们再也受不了了。我们的人越来越快地开始失去战斗力,有的是疾病,是的,但大部分是彻底累垮了,精疲力尽。运输机一次又一次地装载着一只手都抬不动的人。当我的耐力终于耗尽时,援军从空中进入密支那这座被盟军占领的机场。他们是绿色的,勇敢如同地狱来者,因为密支那之战已经到了关键的阶段,我们需要男人——任何类型的男人。新来的美国兵抓住每一个机会与劫掠者交谈,甚至在我们被装进运输机的时候也要寻求建议。
掠夺者中没有一个人是步行回印度的。每个人都是被医护人员命令离开的;每一个在三个月前自豪而自信地进入缅甸的人,要么作为一名伤员被送出,要么被留在缅甸丛林墓地。
在医院,我躺在床上,甚至在我想查看我累积的邮件前一周就放在床上了。我们有两次的货物来自空投,甚至有的是液体货物,多半是酒。在我的床上,这个月是六月,但盒子是家人送来的圣诞礼物。其他乘飞机回来的男孩收到了延迟的礼物,这几乎又像圣诞节一样。然后我们得知,我们中一些甚至没有从病床上爬起来的人被召唤回丛林的地狱。我们知道密支那之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对男人的需求已经到了危急时刻,但我们不敢相信他们在召唤我们。当电话里要求有100名志愿者回来的时候,没有人。
于是,逐渐出现了所谓的梅里美掠夺者的“崩溃”。在医院的房间里,这些人又一次地生活着——那些疲惫的上上下下行走的时光,他们在缅甸的山坡上来回移动,来回走动。他们与苍蝇、水蛭、剥落的灌木丛、雨水、泥土、古老的丛林和死去的日本人的发霉的臭味在一起,以及永远存在的对那些日子的恐惧,一起重温那段日子。埋伏,偶尔的冷嘲热讽,而这种理解不可能有回报。

劫掠者士兵使用75毫米榴弹炮在密支那机场向敌人射击
最后,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回到美国。我们回家了。第一批中有五名军官和大约四百名应征入伍的士兵,其他人则是条件许可。我们回家时听到有人说我们已经崩溃了。但是我们没有。是的,那些必须回去的人确实抱怨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能活下来,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士气崩溃了,也不是因为我们失败了。
梅里尔的劫掠者,我们所有还能走路的人,会再走几千英里去日本接受任务,如果那是我们的使命的话。不,梅里美劫掠者的士气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从来没有退缩过。我们只是疲惫不堪!

史迪威将军在密支那颁发奖章。(General Stilwell awarding medals at Myitkyina.)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2-25 09:19:37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