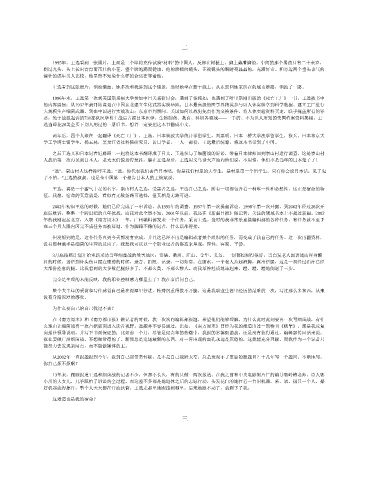Page 8 - 鼠疫围城
P. 8
二
1995年,王选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三个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反绑在树桩上,脚上戴着脚镣。中间的那个男孩只有二十来岁,
剃过光头,头上长出青青而茁壮的小茬,整个脸饱满而健康,他的脸倾向镜头,正视镜头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好奇。和旁边两个垂头丧气的
健壮的成年男人比较,他显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
王选看到这张照片,泪流满面。她多次和我讲到这个情景,当时她坐在新干线上,从东京回她家所在的城市姬路,泪流了一路。
1996年末,王选第一次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中日关系研讨会,遇到了张纯如,也遇到了哈里斯刚出版的《死亡工厂》一书,王选被书中
的内容震惊:从1937年就开始谋划在中国东北建立生化武器实验基地、日本最高级的医学界精英参与以人体实验拿到科学数据、建立工厂进行
大规模生产细菌武器,到在中国进行实战攻击;东京审判期间、美国如何以战犯免责作为交换条件,将人体实验资料买走,联手掩盖所有的罪
恶,免于战犯起诉的731部队医学博士战后占据日本医学、生物制药、教育、科研各领域——一手的、不为世人所知的美国档案资料揭秘。王
选当即花20美金买下别人用过的一册旧书,想着一定要把这本书翻成中文。
两年后,四个人聚在一起翻译《死亡工厂》,王选,日本筑波大学统计学留学生,刘惠明,日本一桥大学法学留学生,徐兵,日本东京大
学工学博士留学生,杨玉林,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访日学者,一人一部份,王选最后统筹,将这本书带到了中国。
之后王选又和日本记者近藤昭二一起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日文。王选参与了细菌战的诉讼,带着日本律师回到崇山村进行调查,这是崇山村
人战后第一次再见到日本人,老太太们惊恐得发抖,躲在王选身后,王选用义乌话大声地向他们说,不用怕,他们不是当年的日本鬼子了!
“选”,崇山村人这样称呼王选。“选,你代表我们去告日本吧,你是我们村里的大学生,是村里第一个留学生,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见了鬼
子不怕。”王选的叔叔、也是全中国第一个想告日本人的王焕斌说。
王选,真是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崇山村人之选,受害者之选,王选自己之选,所有一切都包含着一种唯一性和必然性,这正是宿命的特
征,我想,宿命的真意就是,看似有无数条路可选择,但真相是无路可逃。
2002年初识王选的时候,她们已经完成了一审诉讼,从1995年的调查,1997年第一次提起诉讼,1998年第一次开庭,到2002年经过28次开
庭后败诉,整整一个跨世纪的八年抗战。而我对此全然不知,2001年以前,我还在《新疆日报》做记者,关注的领域基本上不超过新疆。2002
年的我刚定居北京,入职《南方周末》一年,广州编辑部发来一个任务,采访王选。当时的我非常乐意接编辑部的各种任务,有任务就不至于
在三个月大限内因完不成任务而被辞退,作为脚跟不稳的记者,什么活都得接。
但没想到的是,这个任务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并且这已经不再是编辑或者某个组织的任务,而变成了我自己的任务。这一次再翻资料,
没有那种满手是细菌的生理的反应了,我想我可以以一个职业记者的姿态来呈现:理性、客观、平静。
3月底按照计划开始重新采访当年细菌战的受害地区:常德、衢州、江山、金华、义乌。一切都控制得很好,当白发老人因讲述而浑身颤
抖的时候,当烂到骨头伤口摆在眼前的时候,录音、拍照、记录,一切如常。在丽水,一个老人拉起裤脚,露出烂腿,这是一双经过治疗已经
大部份痊愈的腿,比我看到的大多数烂腿好多了,不那么臭,不那么糁人。而我却神经质地站起来,蹬、蹬、蹬地倒退了三步。
完全是生理的本能反映,我的职业控制感力哪里去了?我在事后问自己。
整个大半年的采访和写作感觉自己是在泥潭里行进,粘滞沉重得拔不开腿,这是我职业生涯里经历的最难的一次,写过那么多东西,从来
没有身陷泥潭的感觉。
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找过不去?
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做记者的时候,我一次次向编辑部报题,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此时此刻要再一次写细菌战,有什
么理由让细菌战再一次占据版面进入读者视野。选题并不容易通过,比如,《南方周末》曾经为我的报道出过一期特刊《极罪》,那是我反复
向报社领导说明,并写下书面保证的;比如前一个月,尽管是纪念年的热潮中,我报的常德细菌战,还是没有获得通过,编辑部传回话来说,
报社要做广州细菌战,不想做常德的了。新闻总是追逐最新的东西,对一再出现的面孔永远是厌倦的,这我能充分理解,而我作为一个记者只
能努力去发现新闻点,而不能做媒体的主。
从2002年一直报题报到今年,报到自己都常常怀疑,是不是自己视野太窄,总是发现不了重要的新题目?十几年写一个题目,不断地写,
你自己烦不烦啊?
13年来,跟踪报道王选和细菌战的记者不少,但都不长久,有的只做一两次报道。在我之前有中央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郭岭梅老师,诗人郭
小川的大女儿,几乎跟拍了诉讼的全过程。而这差不多都是她退休之后的志愿行动,头发花白的她扛着一台旧机器,采、录、摄只一个人,架
好机器就得擦汗,整个人天天都在汗流浃背,王选走那里她跟拍到哪里。后来她跟不动了,就剩下了我。
这难道也是我的宿命?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