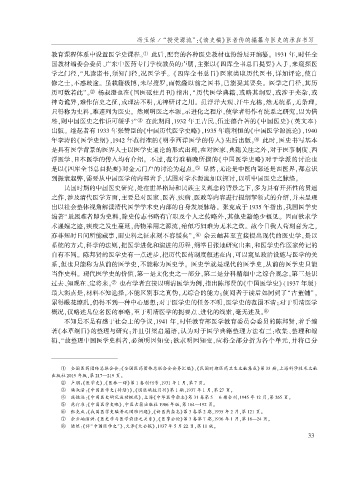Page 31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三期
P. 31
冯玉荣 / “授受源流”:《清史稿》医者传的编纂与医史的承启书写
教育课程体系中设置医学史课程。 ① 此后,配套的各种医史教材也纷纷展开编纂。 1931 年,时任全
国教材编委会委员、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员的卢朋,主张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来窥探医
学之门径,“凡读诸书,须知门径,况医学乎。 《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取历代医书,详加评论,使自
修之士,不惑歧途。 虽载籍极博,未尽搜罗,而乾隆以前之医书,已能提其要矣。 医学之门径,其历
历可数若此”。 ② 杨叔澄也在《国医砥柱月刊》指出,“历代医学典籍,或略其纲要,或涉于芜杂,或
神奇诡异,难作信史之征,或理法不明,无裨研讨之用。 虽洋洋大观、汗牛充栋,然无统系,无条理,
只得称为史料,难遽列为医史。 然则明医之本源,示进化之程序,使学者得作有统系之研究,以为借
鉴,则中国医史之作讵可缓乎?” ③ 在此期间,1932 年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本)
出版。 继起者有 1933 年张赞臣的《中国历代医学史略》,1935 年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1940
年李涛的《医学史纲》,1942 年范行准的《明季西洋医学的传入》先后出版。 ④ 此时,医史书写基本
是具有医学背景的医界人士以医学史通论的形式出现,在对医家、典籍关注之外,对于医事制度、西
洋医学、日本医学的传入均有介绍。 不过,范行准稍晚所撰的《中国医学史略》对于学派的讨论也
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金元门户的讨论为起点。 ⑤ 显然,无论是中医内部还是西医界,都意识
到振衰起弊,需要从中国医学的内部着手,试图对学术源流加以探讨,以明中国医史之脉络。
民国时期的中国医史研究,处在世界格局和民族主义观念的背景之下,多为具有开拓性的贯通
之作,涉及清代医学方面,主要是对医家、医著、疾病、医政等内容进行提纲挈领式的介绍,并未呈现
出以社会整体视角解读清代医学学术史内部的自身发展脉络。 张克成于 1935 年指出,我国医学史
编著“最困难者即为史料,除史传志书略有官职及个人之传略外,其他史籍绝少概见。 因而欲求学
术递嬗之迹,疾疫之发生蔓延,药物采用之源流,殆似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故今日我人苟刻意为之,
亦非短时日间所能蒇事,而史料之征求刻不容缓矣”。 ⑥ 余云岫甚至直接提出现代的医史学,是以
系统的方式,科学的法则,把医学进化和演进的历程,纲举目张地研究出来,和医学史作医家传记的
自有不同。 陈邦贤的医学史有一点进步,把历代医药制度叙述在内,可以窥见政治设施与医学的关
系,但也只能称为从前的医学史,不能称为医史学。 医史学就是现代的医学史,从前的医学史只能
当作史料。 现代医学史的价值,第一是文化史之一部分,第二是分科精细中之综合观念,第三是识
过去、知现在、定将来。 ⑦ 也有学者直接以明清医学为例,指出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1937 年版)
最大弱点是,材料不知选择,不能区别事之真伪,无综合的能力;使阅者于读后如同到了“古董铺”,
累得眼花缭乱,仍得不到一种中心思想;对于医学史的任务不明,医学史的范围不清;对于明清医学
概况,仅略述几位名医的事略,至于明清医学的扼要点、进化的线索,毫无述及。 ⑧
不知是不是有感于社会上的争议,1941 年,时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的陈邦贤,着手编
著《本草纲目》的整理与研究;并且引梁启超语,认为对于医学典籍整理方法有三:收集、整理和编
辑,“故整理中国医学史料者,必须明因知变;欲求明因知变,应将全部分折为各个单元,并将已分
①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会务汇编》,《民国时期医药卫生文献集成》第 33 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17—219 页。
② 卢朋:《医学史》,《医林一谔》第 1 卷创刊号,1931 年 1 月,第 7 页。
③ 杨叔澄:《中国医学史(待续)》,《国医砥柱月刊》第 1 期,1937 年 1 月,第 27 页。
④ 戚铭远:《中国医史研究运动概况》,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第 31 卷第 5— 6 期合刊,1945 年 12 月,第 265 页。
⑤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4—192 页。
⑥ 张克成:《我国医学史编著之困难问题》,《新医药杂志》第 3 卷第 2 期,1935 年 2 月,第 121 页。
⑦ 余云岫演讲:《医史学与医学前途之关系》,《医事公论》第 3 卷第 7 期,1936 年 1 月,第 18—24 页。
⑧ 暗然:《评“中国医学史”》,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22 日,第 11 版。
3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