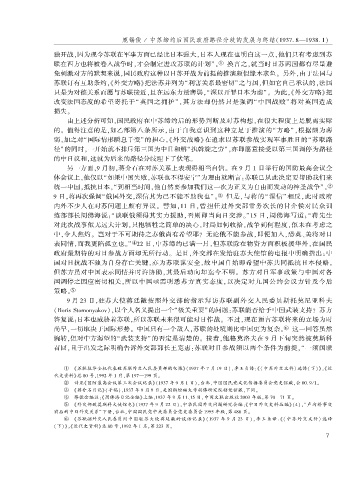Page 5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P. 5
鹿锡俊 / 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路径分歧的发展与终结(1937. 8—1938. 1)
独开战,因为现今苏联在军事方面已经比日本强大,日本人现在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只有考虑到苏
联在西方也将被卷入战争时,才会制定进攻苏联的计划”。 ① 换言之,就当时日苏两国都有尽量避
免刺激对方的默契来说,国民政府这种以日苏开战为前提的推演颇似缘木求鱼。 另外,由于法国与
苏联订有互助条约,《外交方略》把法苏并列为“利害关系最密切”之与国,但如它自己承认的,法国
只是为对德关系而愿与苏联接近,且在远东力量薄弱,“深以开罪日本为虑”。 为此,《外交方略》把
改变法国态度的希望寄托于“ 英国之拥护”,其方法却仍然只是强调“ 中国战败” 将对英国造成
损失。
由上述分析可知,国民政府在中苏缔约后的形势判断及对苏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
的。 值得注意的是,如乙部第八条所示,由于自我意识到这种立足于推演的“方略”,根据颇为薄
弱,加之对“国际情形瞬息千变” 的担心,《外交战略》 在追求以苏联参战实现军事胜日的“苏联路
径”的同时,一开始就不排斥第三国为中日和解“执斡旋之劳”,亦即愿意接受以第三国调停为路径
的中日议和,这就为后来的路径分歧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9 月初,蒋介石在对苏关系上表现得相当自信。 在 9 月 1 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全
体会议上,他仅以“如果中国失败,苏联也不得安宁”为理由就断言:苏联已从此决定要帮助我们来
统一中国,抵抗日本,“到相当时间,他自然要参加我们这一次为正义为自由而发动的神圣战争”。 ②
9 日,蒋再次强调“俄国外交,深信其为己不能不助我也”。 ③ 但是,与蒋的“ 深信” 相反,此时政府
内外不少人在对苏问题上颇有异议。 譬如,11 日,曾担任过外交部常务次长的甘介侯对民众训
练部部长周佛海说:“谈联俄须得其实力援助,否则即当向日交涉。”15 日,周佛海写道:“ 蒋先生
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时局如何收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
中,令人焦灼。 岂对于不可期待之苏俄尚有希望耶? 无论俄不能参战,即便加入,恐英、美将对日
表同情,而我更陷孤立也。” 22 日,中苏缔约已满一月,但苏联除在物资方面积极援华外,在国民
④
政府最期待的对日参战方面却无所行动。 是日,外交部在发给驻苏大使馆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中
国对日抗战不独为自身存亡关键,亦为苏联谋安全,故中国自始即希望中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但苏方虽对中国表示同情并时许协助,其最后动向却迄今不明。 苏方对日军事政策与中国对各
国调停之因应密切相关,所以中国亟需明悉苏方真实态度,以决定对九国公约会议方针及今后
策略。 ⑤
9 月 23 日,驻苏大使蒋廷黻按照外交部的指示拜访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
(Boris Stomonyakov),以个人名义提出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苏联能否给予中国武装支持? 苏方
答复说:日本也威胁着苏联,所以苏联未来很可能对日作战。 不过,现在预言苏联将来的立场为时
尚早,一切取决于国际形势。 中国只有一个敌人,苏联的处境则比中国更为复杂。 ⑥ 这一回答虽然
婉转,但对中方渴望的“武装支持”的否定是清楚的。 接着,鲍格莫洛夫在 9 月下旬突然被莫斯科
召回,且于出发之际明确告诉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苏联对日参战须以两个条件为前提,“一须国联
①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7 年 7 月 19 日),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近
代史资料》总 80 号,1992 年 1 月,第 197—199 页。
② 详见《国防最高会议第三次会议记录》(1937 年 9 月 1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 00. 9 / 1。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 年 9 月 9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④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37 年 9 月 11、15 日,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0—71 页。
⑤ 《外交部致莫斯科大使馆电》(1937 年 9 月 22 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4),“卢沟桥事变
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95 年版,第 488 页。
⑥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同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的谈话记录》 (1937 年 9 月 23 日),李玉贞译:《〈 中苏外交文件〉 选译
(下)》,《近代史资料》总 80 号,1992 年 1 月,第 223 页。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