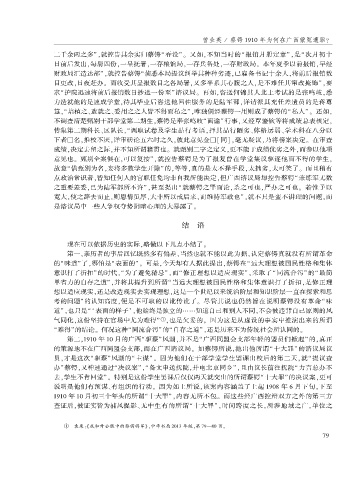Page 77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P. 77
曾业英 / 蔡锷 1910 年为何在广西蒙冤遭驱?
二千余两之多”,就控告其余实归蔡锷“吞没”。 又如,不知当时的“报销月册定章”,是“次月初十
日前后发出,每册四份,一呈抚署,一存粮饷局,一存兵备处,一存财政局。 本年夏季以前报销,早经
财政局汇造达部”,就控告蔡锷“侦悉本局提议纠举其种种劣迹,已雇备书记十余人,将前后报销数
目更改,日夜赶办。 而收受其呈报数目之各局署,又多半系其心腹之人,是不难任其窜改掩饰”,要
求“护院迅速将前后报销数目抄送一份至”谘议局。 再如,咨送何锦其人北上考试的是张鸣岐,悉
力造就他的是速成学堂,待其毕业后咨送他回桂服务的是陆军部,详请派其充任差遣员的是蒋尊
簋,“培植之、造就之、委用之之人皆不得而私之”,唯独偶经蔡锷一用则成了蔡锷的“私人”。 还如,
不调查清楚甄别干部学堂第二期生,蔡锷是奉张鸣岐“面谕”行事,又经覃鎏钦等将成绩总表核定,
传集第二期科长、区队长,“调取试卷及学生品行考语,择其品行陋劣、体格孱弱、学术科在八分以
下者□名,推校不厌,详审磋论五六时之久,彼此意见佥□[同],毫无疑议,乃将榜案决定。 在审查
成绩,决定去留之际,并不知所谓籍贯也。 就甄别二字之定义,更不能于成绩优劣之外,而参以他项
意见也。 甄别全案俱在,可以复按”,就控告蔡锷是为了报复曾在学堂集议驱逐他而不得的学生,
故意“借甄别为名,妄将多数学生开除”的,等等,真的是太不择手段,太拙劣,太可笑了。 而且稍有
点政治常识者,皆知任何人的官职任免均非自我所能决定,但广西谘议局却控告蔡锷“兼练军无数
之重要差委,已为陆军部所不许”,甚至提出“就蔡锷之罪而论,杀之可也,严办之可也。 若惟予以
宽大,使之辞去而止,则恩情虽厚,大非所以戒后来,而维持军政也”,就不只是蛮不讲理的问题,而
是谘议局中一些人争权夺势阴暗心理的大暴露了。
结 语
现在可以依据历史的实际,略做以下几点小结了。
第一,亲历者的事后回忆既然多有偏差,当然也就不能以此为据,认定蔡锷真就没有所谓革命
的“味道”了,哪怕是“表面的”。 可是,今天却有人据此提出,蔡锷在“远大理想被国民性格和集体
意识打了折扣”的时代,“为了避免猜忌”,而“修正理想以适应现实”,采取了“同流合污”的“最简
单省力的自存之道”,并将其提升到所谓“当远大理想被国民性格和集体意识打了折扣,是修正理
想以适应现实,还是改造现实去实现理想,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一直在探索和思
考的问题”的认知高度,便是不可取的以讹传讹了。 尽管其说也仍然旨在说明蔡锷没有革命“味
道”,也只是“‘表面的样子’,他始终是独立的……知道自己和别人不同,不会被违背自己原则的风
气同化,这份坚持在官场中尤为难得” ,也是欠妥的。 因为这是从虚设的事实中推演出来的所谓
①
“难得”的结论。 何况这种“同流合污”的“自存之道”,还是历来不为传统社会所认同的。
第二,1910 年 10 月的广西“驱蔡”风潮,并不是“广西同盟会支部年轻的盟员们掀起”的,真正
的策源地不在广西同盟会支部,而在广西谘议局。 如蔡锷所说,抛出他所谓“十大罪”的谘议局议
员,才是这次“驱蔡”风潮的“主谋”。 因为他们在干部学堂学生罢课出校后的第二天,就“提议查
办”蔡锷,又神速通过“决议案”,“备文申送抚院,并电北京同乡”,且由议长前往抚院“力言总办不
去,学生不肯回堂”。 特别是这份学生罢课后仅仅两天就交出的所谓蔡锷“十大罪”的决议案,更可
说明是他们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 因为如上所说,该案内容涵盖了上起 1908 年 6 月下旬,下至
1910 年 10 月初三个年头的所谓“十大罪”,内容无所不包。 而这些经广西控辩双方之外的第三方
查证后,被证实皆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所谓“十大罪”,时间跨度之长,所涉地域之广,单位之
① 袁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79—80 页。
7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