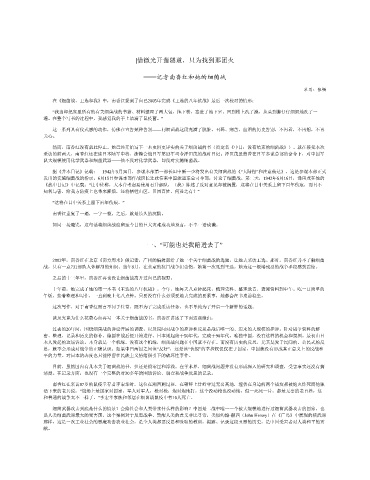Page 33 - 鼠疫围城
P. 33
|借微光开凿隧道,只为找到那团火
——记者南香红和她的细菌战
采写:张畅
在《细菌战、王选和我》中,南香红提到了自己2005年完成《王选的八年抗战》最后一次校对的情形:
“我当即把家里所有的有关细菌战的书籍、材料整理了两大包,拖下楼,塞进了地下室。回到楼上洗了澡,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洗了一
遍。在整个写书的过程中,我感觉我的手上沾满了鼠疫菌。”
这一系列具有仪式感的动作,仿佛在宣告某种告别——同细菌战这段充满了肮脏、丑恶、痛苦、血泪的历史告别,不再看,不再想,不再
关心。
然而,南香红没有就此停止。她已经开始写下一本史料更详实的关于细菌战的书(暂定名《中日: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就在接受本次
采访的前两天,南香红还在读日本陆军中将、浙赣会战日军第13军司令泽田茂的战时日记。泽田茂虽然曾在日军参谋总部的命令下,对中国军
队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他不反对化学武器,却反对实施细菌战。
据《井本日记》记载: 1942年5月30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少将发出有关细菌战的《“大陆指”和注意传达》,这是参谋本部正式
发出的实施细菌战的指示。6月15日参谋本部作战班长辻政信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讨论了细菌战。第二天,1942年6月16日,泽田茂在他的
《战中日记》中记载:“辻中佐称,大本营考虑要使用石井部队,(我)陈述了反对意见却被搁置,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而且不
知利与害,给我方防疫上也带来麻烦,还将牺牲山区、田园百姓,何益之有?”
“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
南香红重复了一遍,一字一顿。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如同一场魔咒,这句话将细菌战遗留至今日的巨大灾难成功地预言,不幸一语成谶。
一、“可能也是我陷进去了”
2002年,南香红在北京《南方周末》做记者,广州的编辑部给了她一个关于细菌战的选题,让她去采访王选。那时,南香红并不了解细菌
战,只有一点731部队人体解剖的知识。当年9月,在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她第一次见到王选。她为这一极端残忍的战争手段感到震惊。
之后的十三年里,南香红再也没让细菌战离开过自己的视野。
十年前,她完成了她的第一本书《王选的八年抗战》。今年,她每天八点钟起床,梳理史料、整理录音、查阅资料到中午。吃一口简单的
午饭,接着整理和写作,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只要没有什么必须要她去完成的要紧事,她都会在书桌前稳坐。
这次写作,对于南香红而言不同于往常,既不为了完成采访任务,也不单纯为了开启一个新鲜的话题。
谈及究竟为什么花费心血再写一本关于细菌战的书,南香红讲述了下面这些缘由:
过去的20年间,围绕细菌战的诉讼开展的调查,以及民间对战争的控诉和反思是战后唯一的、迟来的大规模的控诉。针对战争资料的解
密、整理、记录和历史的修补,德国在战后便开始进行。日本则起始于50年代,完成于90年代。唯独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氛围。最初由日
本人发起的这场诉讼,本身就是一个机缘。没有这个机缘,细菌战问题在中国就不存在。而没有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发于民间的、公民式的反
思,就不会形成对战争的正确认识。如果中日两国之间该“友好”,还是该“仇恨”的掌控权仅仅在于国家,中国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反战和
平的力量。对日本的态度也只能停留在民族主义情绪指引下的破坏性事件。
目前,虽然国内有几本关于细菌战的书,但还是很零星和浮浅。在学术界,细菌战问题并没有形成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受害事实还没有搞
清楚。在记录方面,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对20多年的围绕诉讼、调查和战争反思的记录。
南香红在采访87岁的鼠疫幸存者李宏华时,这位在湘西剿过匪,在朝鲜上甘岭守过无名高地,埋伏在身边的两个战友都被炮火炸死而他独
活下来的老兵说:“战场上是国家对国家,军人对军人,枪对枪,炮对炮地打,这个没动枪也没动炮,但一死死一片,都是无辜的老百姓,这
和普通的战争太不一样了。”李宏华家族和邻居在细菌战鼠疫中有16人死亡。
细菌武器攻击到底是什么的情景?会给社会和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是二战中唯一一个被大规模地进行过细菌武器攻击的国家,也
是人类细菌武器最大的受害国。这个案例对于反思战争、警醒人类的意义非比寻常,类似约翰·赫西(John Hersey)在《广岛》中展现的核武器
那样,这是一次工业社会的恶魔攻击农业社会,是全人类都要反思和吸取的教训,揭露、记录这段丑恶的历史,是中国受害者对人类和平的贡
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