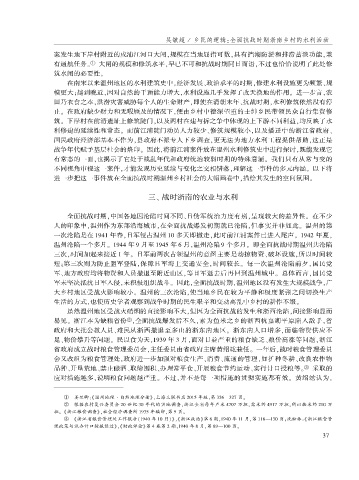Page 35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P. 35
吴敏超 / 乡民的逻辑:全面抗战时期浙南乡村的水利活动
案发生地下岸村附近的戍浦江河口大闸,规模在当地屈指可数,具有挡潮防淤和排涝蓄淡功能,兼
有通航任务。 ① 大闸的规模和修筑水平,早已不可和抗战时期同日而语,不过也恰恰说明了此处修
筑水闸的必要性。
在南宋以来温州地区的水利建筑史中,经济发展、政治承平的时期,修建水利设施更为频繁、规
模更大;越到晚近,因对自然的干预能力增大,水利设施几乎发挥了改天换地的作用。 进一步言,农
田乃衣食之本,洪涝灾害威胁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即使在清朝末年、抗战时期,水利修筑依然没有停
止。 在政府缺少财力和无暇顾及的情况下,便由乡村中德深望重的士绅乡民带领民众自行集资修
筑。 下岸村在前清遗址上修筑陡门,以及两村在建与拆之争中体现的上下游不同利益,均反映了水
利修建的延续性和常态。 而前江浦陡门动员人力较少、修筑规模较小,以及播迁中的浙江省政府、
国民政府经济部基本不作为,县政府不派专人下乡调查,更无法为地方水利工程提供帮助,这正是
战争年代赋予基层社会的烙印。 因此,将前江浦案件放在温州水利修筑史中进行探讨,既能发现它
有常态的一面,也揭示了它处于战乱年代和政府统治较弱时期的特殊意涵。 我们只有从常与变的
不同视角审视这一案件,才能发现历史延续与变化之交相错落,理解这一事件的多元内涵。 以下将
进一步把这一事件放在全面抗战时期温州乡村社会的大幅画卷中,描绘其发生的空间氛围。
三、 战时浙南的农业与水利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各地因沦陷时间不同、日伪军统治力度有别,呈现较大的差异性。 在不少
人的印象中,温州作为东部沿海城市,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就已沦陷,但事实并非如此。 温州的第
一次沦陷是在 1941 年春,日军侵占温州 10 多天即撤走,此时前江浦案件已进入尾声。 1942 年夏,
温州沦陷一个多月。 1944 年 9 月至 1945 年 6 月,温州沦陷 9 个多月。 即全面抗战时期温州共沦陷
三次,时间加起来接近 1 年。 日军前两次占领温州的意图主要是劫掠物资、破坏设施,所以时间较
短;第三次则为防止盟军登陆,保障日军海上交通安全,时间较长。 每一次温州沦陷前夕,国民党
军、地方政府均将物资和人员撤退至附近山区,等日军退去后再回到温州城中。 总体而言,国民党
军未坚决抵抗日军入侵,未积极组织战斗。 因此,全面抗战时期,温州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广
大乡村地区受战火影响较小。 温州的三次沦陷,使当地乡民在较为平静和极度紧张之间切换生产
生活的方式,也使历史学者观察到战争时期的民生艰辛和变动离乱中乡村的耕作不缀。
虽然温州地区受战火硝烟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因为全面抗战的发生和浙西沦陷,间接影响显而
易见。 浙江本为缺粮省份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素为鱼米之乡的浙西杭嘉湖平原陷入敌手,省
②
政府和大批公教人员、难民从浙西撤退至多山的浙东南地区。 浙东南人口增多,面临物资供应不
足、物价攀升等问题。 民以食为天,1939 年 3 月,面对日益严重的粮食缺乏、粮价高涨等问题,浙江
省政府成立战时粮食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兼任。 一年后,战时粮食管理委员
会又改组为粮食管理处,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粮食生产、消费、流通的管理,如扩种冬耕、改良农作物
品种、开垦荒地、禁止酿酒、取缔囤积、办理常平仓、开展粮食节约运动、实行计口授粮等。 ③ 采取的
应对措施越多,说明粮食问题越严重。 不过,并不是每一项措施的贯彻实施都有效。 黄绍竑认为,
① 姜竺卿:《温州地理·自然地理分册》,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326—327 页。
② 根据农村复兴委员会 20 世纪 30 年代的实地调查,浙江全省每年产米 4707 万担,需米约 4917 万担,所以缺米约 210 万
担。 《浙江粮食调查》,社会经济调查所 1935 年编印,第 9 页。
③ 《浙江省粮食管理处工作报告(1940 年 10 月)》,《浙江政治》第 8 期,1940 年 11 月,第 116—130 页;沈松林:《浙江粮食管
理政策与试办计口授粮经过》,《财政评论》第 4 卷第 2 期,1940 年 8 月,第 89—100 页。
3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