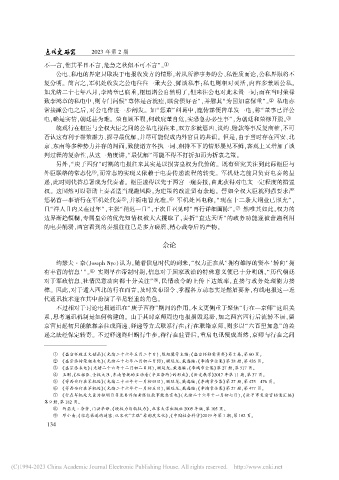Page 135 - \2023年3-4月
P. 135
2023 年第 2 期
不一言,惟其平日不言,危急之秋似不可不言”。 ①
公电、私电的界定只取决于电报收发方的情形,若从所涉事务的公、私性质而论,公私界限将不
复分明。 简言之,军机处收发之公电往往一秉大公、鲜谈私事;私电则相对灵活,内容多兼顾公私。
如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李鸿章已病重,枢垣诸公自然明了,但来往公电对此未置一词;而在当时荣禄
致李鸿章的私电中,则专门问候“尊体是否就痊,眠食俱好否”,并慰其“为国加意保重”。 ② 私电亦
常接踵公电之后,对公电作进一步阐发。 如“惩董”纠葛中,鹿传霖便曾单发一电,称“董事已详公
电,确是实情,朝廷甚为难。 荣自顾不暇,何敢庇董自危,实恐急办必生事”,为朝廷和荣禄开脱。 ③
统观行在枢臣与全权大臣之间的公私电报往来,双方多就惩凶、议约、赔款等事反复商榷,不可
否认这有利于群策群力、探寻最优解,并尽可能促成内外官员的共识。 但是,由于当时存在西安、北
京、东南等多种势力并存的局面,致使诸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的情形屡见不鲜,客观上又增加了谈
判过程的复杂性,从这一角度讲,“最优解”可能不得不打折扣而为折衷之策。
另外,“庚子西狩”时期的电报往来其实是以损害皇权为代价的。 既有研究关注到此际枢臣与
外臣联络的常态化 ,而常态的实现又依赖于电奏传递流程的转变。 军机处之前只负责电奏的呈
④
递,此时则代替总署成为代奏者。 枢臣遂得以先于两宫一窥奏报,由此获得对电文一定程度的措置
权。 这固然可以帮助上奏者适当规避风险,为建策的改进留有余地。 譬如全权大臣就列强要求严
⑤
惩祸首一事请行在军机处代奏 ,并祈电旨允准。 ⑥ 军机处回电称,“现在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
且“洋人日内又在过年”,主张“稍迟一日”,于次日召见时“再行详细面陈”。 ⑦ 然唯其如此,权力的
边界渐趋模糊,专属皇帝的优先知情权被大大攫取了,奏折“直达天听”的政务功能遂被普遍利用
的电奏削弱,两宫看到的奏报往往已是多方磋磨、精心裁夺后的产物。
余论
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
有丰富的信息’”。 ⑧ 实则早在帝制时期,信息对于国家政治的特殊意义便已十分明朗,“历代朝廷
对于军政信息、社情民意动向都十分关注” ,民情政令的上传下达效率,直接与政务处理能力接
⑨
榫。 因此,对于遁入西北的行在而言,及时发布诏令、掌握各方动态实是燃眉要务,有线电报这一近
代通讯技术遂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不过相对于讨论电报通讯在“庚子西狩”期间的作用,本文更侧重于聚焦“行在—京师”这组关
系,思考通讯机制是如何构建的。 由于其时京师周边电报损毁迟滞,加之两宫西行后流转不居,留
京官员起初只能依靠亲往或商递、驿递等方式联系行在;行在联络京师,则多以“六百里加急”的差
递之法经保定转寄。 不过驿递终归蜗行牛步,待行在驻晋后,重启电讯便成当然,京师与行在之间
① 《盛宣怀致王文韶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第 2 卷,第 60 页。
② 《盛宗丞转荣相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到),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 28 册,第 426 页。
③ 《盛宗丞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到),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 27 册,第 517 页。
④ 王刚:《从枢臣、全权大臣、东南督抚的互动看〈辛丑条约〉的形成》,《历史教学》2017 年第 11 期,第 37 页。
⑤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 27 册,第 475—476 页。
⑥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 27 册,第 477 页。
⑦ 《行在军机处大臣为拟明日召见再详细面陈议款事致北京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第 9 册,第 182 页。
⑧ 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5 页。
⑨ 邓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第 102 页。
1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