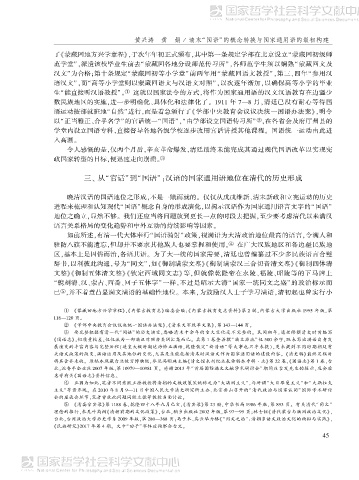Page 44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P. 44
黄兴涛 黄 娟 / 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
了《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于次年年初正式颁布,其中第一条规定学部在北京设立“蒙藏回初级师
范学堂”,派遣该校毕业生前去“蒙藏回各地分设师范传习所”,各师范学生须以娴熟“蒙藏回文及
汉文”为合格;第十条规定“蒙藏回初等小学堂”前两年用“蒙藏回语文教授”,第三、四年“参用汉
语汉文”,而“高等小学堂则以蒙藏回语文与汉语文对照”,以次逐年渐加,以确保高等小学的毕业
生“能直接听汉语教授”。 ① 这就以国家法令的方式,将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汉文汉语教育在边疆少
数民族地区的实施,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和法律化了。 1911 年 7—8 月,清廷已没有耐心等待国
语运动按部就班地“自然”进行,而是着急颁行了《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明令
以“正当雅正、合乎名学”的官话统一“国语”,“由学部设立国语传习所” ,在各省会及府厅州县的
②
学堂内设立国语专科,直接督导各地各级学校逐步改用官话讲授其他课程。 国语统一运动由此进
入高潮。
令人感慨的是,仅两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最终未能完成其通过现代国语改革以实现宪
政国家转型的目标,便迅速走向崩溃。 ③
三、 从“官话”到“国语”:汉语的国家通用语地位在清代的历史形成
晚清汉语的国语地位之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仅仅从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的历史
进程来梳理和认知现代“国语”概念自身的形成演化,以揭示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语”
地位之确立,显然不够。 我们还应当将问题放到更长一点的时段去把握,至少要考虑清代以来满汉
语言关系格局的变化趋势和中外互动的持续影响等因素。
如前所述,有清一代大体奉行“国语骑射”政策,视满语为大清政治地位最高的语言,令满人和
驻防八旗不能遗忘,但却并不要求其他族人也要掌握和使用。 ④ 在广大汉族地区和各边疆民族地
区,基本上是因俗而治,各语其语。 为了大一统的国家需要,清廷也曾编纂过不少多民族语言合璧
辞书,以利彼此沟通,号为“同文”,如《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满蒙汉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
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 《钦定西域同文志》 等,但就像乾隆帝在永陵、福陵、昭陵等的下马牌上
“镌刻清、汉、蒙古、西番、回子五体字”一样,不过是昭示大清“国家一统同文之盛”的政治标示而
已 ,并不着意凸显满文满语的基础性地位。 本来,为鼓励汉人士子学习满语,清初起也曾实行小
⑤
① 《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内蒙古教育志》 编委会编:《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 第 2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8—120 页。
② 《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 143—144 页。
③ 要完整把握有清一代“国语”的历史演变,忽略清末十余年的重大变化是不完整的。 民国初年,遗老修撰清史时曾编写
《国语志》,但质量较差,仅仅流为一部满汉对照分类词汇集而已。 其第 1 卷奎善撰“满文源流”仅 500 余字,既未写出满语自身发
展演变的丰富内容与完整历程(连皇太极时期达海修正满语,乾隆钦定“新清语” 等大事也只字未提),更未提到不同时期朝廷有
关语文政策的改变、满语运用及其地位的变化,尤其是未能包括清末时汉语文作为国家通用语的建设内容。 《清史稿》最终定稿时
将其舍弃未收。 原稿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见冯明珠主编《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稿本专辑·志》第 22 卷,《国语志》第 1 卷,台
北,沉香亭企业社 2007 年版,第 10979—10981 页。 感谢 2013 年“首届国际满文文献学术研讨会”期间庄吉发先生的提示,及会后
惠寄有关《国语志》资料信息。
④ 正因为如此,笔者不同意欧立德教授将清朝的文教政策笼统称之为“大满洲主义”,与所谓“大日耳曼主义”和“大斯拉夫
主义”等量齐观。 在 2010 年 8 月 9—11 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北京香山召开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
会的座谈会环节,笔者曾就此问题同欧立德等教授当面讨论。
⑤ 《清高宗实录》第 1188 卷,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己亥,《清实录》第 23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893 页。 有关清代“同文”
理念的推行,参见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台北,稻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7—99 页;林士铉《清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化》,
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2009 年版,第 280—368 页;马子木、乌云毕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
《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 文中“回子”字体应指察合台文。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