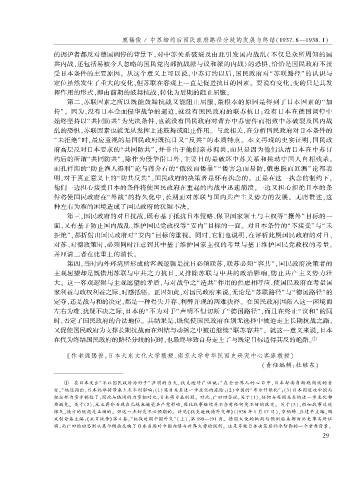Page 27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P. 27
鹿锡俊 / 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路径分歧的发展与终结(1937. 8—1938. 1)
的拥护者都反对德国调停的背景下,对中苏关系破裂及由此引发国内战乱(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国
共内战,还包括易被今人忽略的国民党内部抗战派与议和派的内战)的恐惧,恰恰是国民政府不接
受日本条件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苏订约以后,国民政府对“苏联路径”的认识与
定位虽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苏联在客观上一直是促进抗日的因素。 要说有变化,变的只是其发
挥作用的形式,即由前期的鼓舞抗战,转化为后期的阻止屈服。
第二,苏联因素之所以既能鼓舞抗战又能阻止屈服,最根本的原因是得到了日本因素的“加
持”。 因为,没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逼迫,就没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没有日本在德国调停中
始终坚持以“共同防共”为先决条件,也就没有国民政府对背弃中苏密件而招致中苏破裂及国内战
乱的恐惧,苏联因素也就无从发挥上述鼓舞或阻止作用。 与此相关,在分析国民政府对日本条件的
“未拒绝”时,最应重视的是国民政府既抗日又“反共”的本质特点。 本文再现的史实证明,国民政
府高层反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并非由于他们亲苏拥共,而只是因为他们认清日本在中苏订
约后的所谓“共同防共”,除作为侵华借口外,主要目的是破坏中苏关系和挑动中国人自相残杀。
而孔祥熙的“防止渔人得利”论与蒋介石的“俄狡而倭暴” “倭害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 论都表
明,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防共反共”,国民政府的决策者是怀有执念的。 正是在这一执念的制约下,
他们一边担心接受日本的条件将使国民政府在重起的内战中迅速崩溃,一边又担心拒绝日本的条
件将使国民政府在“外战”的持久化中,长期面对苏联与国内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 无庸赘述,这
种左右为难的困境造成了国民政府的犹疑不决。
第三,国民政府的对日抗战,既有基于抵抗日本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等“攘外”目标的一
面,又有基于防止国内战乱、维护国民党政权等“安内”目标的一面。 对日本条件的“不接受”与“未
拒绝”,都折射出国民政府对“安内”目标的重视。 同时,它们也说明,在评析此期国民政府的对日、
对苏、对德政策时,必须同时注意到其中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考量与基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考量,
并厘清二者在比重上的消长。
第四,当时内外环境所形成的客观逻辑是抗日必须联苏,联苏必须“容共”,国民政府决策者的
主观愿望却是既借用苏联与中共之力抗日,又排除苏联与中共的政治影响,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壮
大。 这一客观逻辑与主观愿望的矛盾,与对战争之“造共”作用的焦虑相呼应,使国民政府在考量国
家利益与政权利益之际,时感抵牾。 正因如此,对国民政府来说,无论是“苏联路径”与“德国路径”的
定夺,还是战与和的决定,都是一种得失并存、利弊并现的两难抉择。 在国民政府因陷入这一困境而
左右为难、犹疑不决之际,日本的“不为对手”声明不但切断了“德国路径”,而且在终止“议和”的同
时,否定了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 其结果是,既促使国民政府在别无选择中被迫走上长期抗战之路,
又促使国民政府为支撑长期抗战而在纠结与动摇之中被迫继续“联苏容共”。 就这一意义来说,日本
在代为终结国民政府的路径分歧的同时,也最终导致自身走上了与既定目标适得其反的绝路。 ①
〔作者鹿锡俊,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杜继东)
① 在日本发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声明的当天,狄克逊对广田说:“ 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日本却要负断绝商谈的责
任。”他还指出,日本此举将带来 3 点不利影响:(1)英日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危险;(2)中国的“布尔什维化”;(3)日本因进攻中国而
把全部力量牵制住了,因此与俄国的力量相对比,日本将日益削弱。 对此,广田回答说,关于(1),任何与英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都
要避免。 关于(2),反正蒋介石现在已越来越受共产党影响,因此战事继续并不会有任何更不好的改变。 关于(3),假如战事迁延
很久,德方的忧虑是正确的。 但这一点却是不必预期的。 详见《狄克逊致德外交部》(1938 年 1 月 17 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陶
文钊分卷主编:《抗日战争》第 4 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上),第 190—191 页。 德国大使的批判与预测后来都为历史事实所证
明,而广田的回答则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当局对中国内情与世界大势的误判。 这是导致日本决策层利令智昏的一个重要背景。
2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