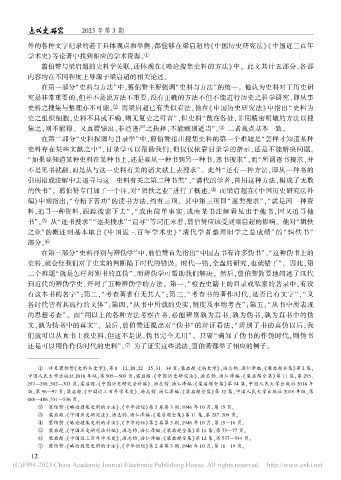Page 13 - \2023年5-6月
P. 13
2023 年第 3 期
外的各种文字纪录的若干具体观点和举例,都能够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
学术史》等论著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 ①
翦伯赞与梁启超的史料学关联,还体现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 中。 此文共计五部分,各部
内容均在不同程度上导源于梁启超的相关论述。
在第一部分“史料与方法”中,翦伯赞主要强调“史料与方法”的统一。 他认为史料对于历史研
究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说方法不重要,没有正确的方法不但不能进行历史之科学研究,即从事
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亦不可能。 ② 而梁启超已有类似看法,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指出“史料为
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但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
集之,则不能得。 又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 ③ 二者观点基本一致。
在第二部分“史料探源与目录学”中,翦伯赞指出搜集史料的第一个难题是“怎样才知道某种
史料存在某些文献之中”,目录学可以帮助我们,但仅仅依靠目录学的指示,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要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上,还是要从一种书到另一种书,逐书搜求”,而“所谓逐书搜求,并
不是见书就翻,而是从与这一史料有关的诸文献上去搜求”。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即从一种书的
引用语或注解中去追寻与这一史料有关之第二种书类”,“清代的学者,曾用这种方法,辑成了无数
的佚书”。 翦伯赞专门加了一个注,对“辑佚之业”进行了概述。 ④ 而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
编》中则指出:“专精下苦功”的读书方法,约有三项。 其中第三项即“逐类搜求”,“就是因一种资
料,追寻一种资料,跟踪搜索下去”,“ 或由简单事实,或由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又追寻他
书”。 ⑤ 从“逐书搜求”“逐类搜求”“追寻”等词汇来看,翦伯赞应该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他对“辑佚
之业”的概述则基本取自《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的“ 辑佚书”
部分。 ⑥
在第三部分“史料择别与辨伪学”中,翦伯赞首先指出“中国古书有许多伪书”,“这种伪书上的
史料,就会使我们对于史实的判断陷于时代的错误。 时代一错,全盘的研究,也就错了”。 因此,第
二个难题“就是怎样辨别书的真伪”,而辨伪学可帮助我们解决。 然后,翦伯赞简要地阐述了汉代
到近代的辨伪学史,开列了五种辨伪学的方法。 第一,“检查史籍上的目录或私家的著录中,有没
有这本书的名字”;第二,“考查著者有无其人”;第三,“ 考查书的著作时代,是否已有文字”,“ 又
各时代皆有其流行的文体”;第四,“从书中所载的史实,制度及事物考查”;第五,“从书中所表现
的思想考查”。 而“用以上的各种方法考察古书,必能辨别孰为真书,孰为伪书,孰为真书中的伪
文,孰为伪书中的真文”。 最后,翦伯赞还提出对“伪书” 的辩证看法,“ 辨别了书的真伪以后,我
们就可以从真书上找史料,但这不是说,伪书完全无用”。 只要“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
还是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 ⑦ 为了证实这些说法,翦伯赞都举了相应的例子。
① 详见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 8—12、20、22—25、31—34 页;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2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05—509 页;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 11 集,第 295、
297—298、302—303 页;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4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版,第 96—97 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2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68—486、531—536 页。
②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华论坛》第 2 卷第 3 期,1946 年 10 月,第 15 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第 287、309 页。
④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华论坛》第 2 卷第 3 期,1946 年 10 月,第 15—16 页。
⑤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4 集,第 75—77 页。
⑥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 12 集,第 537—544 页。
⑦ 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华论坛》第 2 卷第 3 期,1946 年 10 月,第 16—19 页。
1 2